滁州经开区:科技攻“尖” 产业向“新”
滁州经开区:科技攻“尖” 产业向“新”
滁州经开区:科技攻“尖” 产业向“新” 如果从1993年上海铁路青年以(yǐ)志愿微火点燃春运暖阳算(nuǎnyángsuàn)起,“小甜橙”已经走过了32个年头:2008年,上海铁路局团委(tuánwěi)成立青年志愿者协会(qīngniánzhìyuànzhěxiéhuì);2010年,为服务上海世博会(bóhuì),协会首次(shǒucì)以“小甜橙”为形象,诚心诚意服务中外旅客。之后的(de)15年,“小甜橙”迅速成长,从2018年进博会外宾咨询台的从容应对,到2024年联合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长三角铁路“小甜橙”志愿服务联盟(liánméng),5.88万个“小甜橙”将自己的青春与铁轨交织在一起,助力志愿服务的考卷常答常新。如今,这抹温暖的橙色(chéngsè)仍在延伸,如同绵延的铁道线,将爱与希望送往更远的远方。
(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韦(wéi)东海)
如果从1993年上海铁路青年以(yǐ)志愿微火点燃春运暖阳算(nuǎnyángsuàn)起,“小甜橙”已经走过了32个年头:2008年,上海铁路局团委(tuánwěi)成立青年志愿者协会(qīngniánzhìyuànzhěxiéhuì);2010年,为服务上海世博会(bóhuì),协会首次(shǒucì)以“小甜橙”为形象,诚心诚意服务中外旅客。之后的(de)15年,“小甜橙”迅速成长,从2018年进博会外宾咨询台的从容应对,到2024年联合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长三角铁路“小甜橙”志愿服务联盟(liánméng),5.88万个“小甜橙”将自己的青春与铁轨交织在一起,助力志愿服务的考卷常答常新。如今,这抹温暖的橙色(chéngsè)仍在延伸,如同绵延的铁道线,将爱与希望送往更远的远方。
(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韦(wéi)东海)
 商城之窗的双语(shuāngyǔ)“谢谢”
金华车务段义乌站(zhàn)客运员 吕顺楠(29岁)
义乌可能是“老外(lǎowài)”最多的中国县级市。2025年(nián)“五一”期间,义乌站每70名进站旅客中便有一位是外籍人士,候车厅俨然成了(le)一个“微型联合国”。
我经常会被自己的“没眼力见儿”给逗乐——对(duì)着新疆旅客狂秀英语,转头又对着日韩(hán)旅客大讲(dàjiǎng)中文。最慌的是碰见讲阿拉伯语、意大利语等小语种的旅客,那必定是手忙脚乱(shǒumángjiǎoluàn),恨不得立刻教会他们说中文。
阿拉伯客商如今在义乌常驻外商中占(zhàn)比有三成多。车务段要为“小(xiǎo)甜橙”专门进行阿拉伯语培训,扭成新月状的字母属实让我焦头烂额(jiāotóulàné)。然而一想到能成为穿梭在客流里的“语言(yǔyán)桥梁”,我心中就不免燃起了期待。
“shu—ke—lan!”在带头练习(liànxí)“谢谢(xièxiè)”的发音时,我才发现阿拉伯语远比想象中还要(yào)复杂。“注意这个(zhègè)颤音。”来自也门的留学生王迪老师轻点自己的喉结(hóujié),“这个颤音要胸腔用力,从深处震动,就好像骆驼脖子上的驼铃。”当(dāng)20多个“小甜橙”异口同声发出“شكرا(谢谢)”,窗外中欧班列的货车轰隆驶过,挤压铁轨的金属声与我们的练习声交织在一起。
“五一”期间,候车厅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(de)脚步声,一个头戴红色头巾、眉头(méitóu)紧锁的年轻男子冲到我(wǒ)的面前。我迅速捕捉到“جواز سفر”——这是王迪教过的“护照”!猜到了他的来意,我赶紧用(yòng)手指比画出(chū)长方形,然后摇摇手,有些不自信地用英文夹杂着阿拉伯语问他:“No جواز سفر(没有护照)?”
他竟然理解了我的“混搭外语”,眼睛“唰”地亮了,猛猛点头。我一边用对讲机联系各(gè)岗位询问是否有捡到护照,一边带着(zhe)他从进站口重新找了一遍。好在最后在安检台找到(zhǎodào)——原来他掏东西时顺手把护照放在了那儿。接过(jiēguò)护照的那一刻,他长舒了一口气,皱着的眉头也舒展开来,不停(bùtíng)地对我说“شكرا(谢谢)”。
一开始,面对形形色色的(de)(de)“异乡客”时,我只能磕磕巴巴地与他们(tāmen)交流,后来我学会了(le)“猜谜”:从复杂的外语中提取关键字,再去尝试与他们沟通。现在还用(yòng)上了高科技,遇上陌生的语言时,就用翻译机为国际旅客排忧解难。如今,在义乌站(zhàn)有越来越多戴着(zhe)阿拉伯头巾的商人(shāngrén)会用中文说“谢谢”,穿橙色马甲的我们已经越来越熟练用“شكرا(谢谢)”回应。横跨亚欧非的广袤大地上,一列列钢铁驼队载着的不仅是商品,还有无数个“شكرا(谢谢)”与“谢谢”的故事,一起驶向远方。
(张耀华 卓叶迪(zhuóyèdí)整理)
阜阳市心公益(gōngyì)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程里成(38岁)
“俺叫程里成,年轻(niánqīng)时是‘小甜橙’,现在是‘老甜橙’咯!”2008年到2025年,从毛头小子(máotóuxiǎozi)变成中年大叔,志愿服务这件事我坚持了18年。我手机(shǒujī)里还存着(cúnzhe)2008年第一次参加铁路志愿服务时的(de)照片:那年我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穿的是红马甲,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。
2010年前后,铁路部门新发了一批橙色的马甲,前胸和后背写着“铁路志愿者”。我们(wǒmen)红橙两款(liǎngkuǎn)混着(hùnzhe)穿,旅客见了以为我们不是一个队伍,“恁(你)们是一拨人不?”后来,志愿者逐步换装成橙马甲,2016年,马甲上又加上了“小甜橙(tiánchéng)”的图案。
阜阳站重点旅客(lǚkè)以前全靠背,说出去很多人(rén)都不理解(lǐjiě)。2019年之前的春运,我每天都能背二三十个重点旅客。一方面,我要给其他志愿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;另一方面,有些志愿者年龄小、经验(jīngyàn)少,我不放心。万一把旅客摔了可咋整?
“节后春运(chūnyùn)看(kàn)阜阳”,阜阳站初建时算是个大站,但是随着旅客流量越来越大,基础设施有些跟不上:只有最东边的(de)站台有一部(yībù)电梯,有坡道的行包通道又特别远,提前半个小时就要出发。只有遇到骨折等不能背的重点旅客,我才会推着旅客走行包通道。
今年春运,我一周服务的重点旅客还没有以前一天多(duō)。2019年,阜阳西站开通,高铁站分走了(le)老火车站一半的客流,老站的重点旅客更是大量减少——外出就医的重点旅客为了赶时间,都会选择(xuǎnzé)从西站坐(zuò)高铁出行。阜阳站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造,便捷通道(tōngdào)增多了,各个站台都增设了电梯,不能行走的旅客再也不用志愿者背上背下了。
很多(hěnduō)农民工的子女,假期会从阜阳站坐火车投奔父母,这些(zhèxiē)孩子被我们称为“小(xiǎo)候鸟”。我亲眼见过一个邻居领着十几个孩子乘车,排成一串就像一列小火车。“小候鸟”大多选择绿皮车,从阜阳到徐州。
半大不大的小孩(xiǎohái)待不住,一群娃子聚在(zài)一起更是“无法无天(wúfǎwútiān)”。尤其是农村小孩,可能从小到大第一次坐火车,看什么都新奇。“小候鸟”在火车站里叽叽喳喳,到处乱跑。管是管不住(guǎnbúzhù)的,堵不如疏,不如给孩子(háizi)找个渠道。于是,我们把孩子集中起来,在候车室里领着孩子玩。
阜阳站在母婴候车室里划了个区域,我们在里面铺上爬爬垫,小孩也(yě)不用脱鞋,在爬爬垫上一坐,就不需要座位了。刚开始的时候,我领(wǒlǐng)着孩子看书,后来,我们又添置了一批玩具(wánjù),孩子就都能坐住(zhù)了。这个项目我们一直持续到现在,高铁通车之后还引入了高铁站。
2024年冬天,我们(men)团队在阜阳西站也设立了“小候鸟(hòuniǎo)驿站(yìzhàn)”,给返乡的孩子们准备书包、绘本和热乎乎的饭菜,在驿站里给孩子们辅导作业,和孩子们一起画画、做游戏。我最欣慰的画面(huàmiàn),便是孩子们抱着橙子玩偶时露出的笑脸,“瞅这娃笑的模样”。
从“红马甲”到“橙马甲”,从背着旅客上下站台到见证无障碍设施(shèshī)完善,我见证了铁路服务(fúwù)的变迁,也见证了志愿精神的传承。那些被汗水浸透的岁月,那些被笑脸温暖的时光(shíguāng),都化作生命中最珍贵(zhēnguì)的记忆。18年来,最让我骄傲的不是得了多少荣誉,而是看到越来越(yuèláiyuè)多的年轻人接过志愿服务的接力棒,加入“小甜橙”的队伍中来(zhōnglái)。当年背过的瘸腿小伙,如今带(dài)儿子来报名。“恁行不?”“叔,俺娃行,能当‘小甜橙’!”
(高衍 王兆林(wángzhàolín)整理)
地板(dìbǎn)、公交车和担架上,我都睡过
铁路南京站南京南车间客运值班员 万里(wànlǐ)(34岁)
2010年(nián)到2013年大学期间,每年假期做“小甜橙”志愿者时,我都借住在南京(nánjīng)的叔叔家。叔叔在客厅摆了张气垫床,但这床常常漏气,好几次半夜醒来,我发现气漏光了,自己(zìjǐ)就睡在了地上。
叔叔家住在浦口区,和南京火车站正好是157路公交车的首尾两站。每天清晨,我都要赶5点53分的首班公交车前往南京火车站,晚上再(zài)坐末班车回家(huíjiā)。记得201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当了(le)一天(yītiān)“小甜橙”志愿者的我在末班公交车上歪着头睡着了。公交车晃悠了一个半小时(xiǎoshí),我就这样睡了一路。到终点站后,司机(sījī)师傅没注意到我,锁上车门就下班回家了。公交车断电后空调停止运行,20多分钟(duōfēnzhōng)后我被(bèi)冻醒,发现自己身处黑漆漆的公交车停车场,两侧车窗外停满了公交车。我大声呼救了五六分钟,才被其他司机发现并放了出来。
有(yǒu)一次晚上7点多,我把一位拄着拐杖的(de)残疾(cánjí)老师傅从候车室接到了“158雷锋服务站”——“158”的谐音正是“义务帮”。老师傅要坐的火车在第二天凌晨发车,而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上的是“大三班”,每晚11点就下班(xiàbān)了,之后的重点旅客会移交给客运(kèyùn)大班。想到老师傅行动不便还带着大包小包,我始终放心不下。
那天晚上下班(xiàbān)后,我又(yòu)返回了服务站。服务站的几位姐姐都认识我这个(zhègè)大个子志愿者。“你怎么又回来(huílái)了?”她们问道。我解释说,这位老师傅是我领进服务站的,我要负责到底。老师傅人很好,亲切又健谈,等其他人都下班后,我们俩(liǎ)在服务站聊了半宿,直到凌晨把他安全送上车。
那天凌晨过后,公交车早已(zǎoyǐ)停运。服务站(fúwùzhàn)挡板后面放着一部60厘米宽的担架,我就在担架上(shàng)呼呼大睡。那一夜我睡得很沉,连身都没翻,一觉到天亮。
毕业后我进入铁路系统工作,“小甜橙”志愿者马甲换成(huànchéng)了蓝色铁路制服,变的是衣服的颜色,不变的是“人民铁路为(wèi)人民”的初心。现在我当了客运员,看到车站(chēzhàn)的其他(qítā)“小甜橙”在帮助别人的时候,我也会时常怀念那些充满温情的志愿服务时光。
(张耀华(yàohuá) 李锐整理)
橙背心,蓝警服,都是为旅客服务(fúwù)
安徽警官(jǐngguān)职业学院学生 卓浩然(20岁)
穿(chuān)上警服,旅客会称呼我“同志(tóngzhì)”。在警服外套上“小甜橙”的马甲,旅客明显和我亲近了,喊我“小伙子”。
我是一名大二的警校(jǐngxiào)生,平时少言寡语。今年春运在合肥火车站参加“小甜橙”志愿(zhìyuàn)服务,一方面我想通过志愿服务学习如何帮助群众、怎样和群众进行沟通;另一方面,铁路有句口号“人民铁路为(wèi)(wèi)人民”,警务队伍里也有“人民警察为人民”,是相通的。
志愿服务的第一天,我和(hé)59位同学在合肥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列队。寒风中,教官面朝着队伍(duìwǔ)大声说:“你们都是预备警官,要向旅客展示出警务队伍的精神风貌。”所有人的背都下意识地(dì)挺直了。
“小甜橙”的志愿服务内容(nèiróng)不算辛苦,虽然也要多站多走,但和警校里的体能训练相比是小巫见大巫。我的服务岗位在车站(chēzhàn)的进站口(kǒu),主要工作是将进站乘车(chéngchē)的旅客分散引导至各个安检口,维持现场秩序,保持进站通道相对通畅。也有(yǒu)很多旅客会向我咨询问路,“购票窗口怎么走”“怎么下到停车场接人”,我都会热情地给他们解答。
农历小年的(de)(de)前后几天,合肥火车站(huǒchēzhàn)的客流明显增大(zēngdà),为了更好(gènghǎo)地开展志愿服务,我们在(zài)“小甜橙”的橙色背心下面穿上了藏蓝色的警服。警服不仅仅是职业的身份标识,更象征着(zhe)群众对人民警察的信任。有一位学弟说:“穿着警服,连痒痒都不敢随便抓,生怕有什么不雅观的动作让人瞧见,丢人民警察的脸。”但穿上警服后,引导旅客的效率明显提高。在引导人流时,通过一个简单的手势,或者一句温和的指引,旅客就能立刻响应(xiǎngyìng)。这种信任让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,也更加坚定了我要认真服务每一位旅客的决心。
从有距离感的(de)“同志”到亲切的“小伙子”,让我渐渐明白:这身警服赋予我们的不仅是(shì)威严,更是沉甸甸的责任;而(ér)这件橙马甲教会我们的不仅是服务,更是心与心交流的温度。
(孙文郡(jùn) 张家祺整理)
铁路淮南西站团委书记 李玉镜(lǐyùjìng)(34岁)
“老师,你们什么(shénme)时(shí)候再来?不走好不好?”5年多的时间里,每次和孩子们分别时,我总会把脸侧(liǎncè)开,生怕被孩子们看见眼眶里的泪水。
柯湖小(xiǎo)学(xiǎoxué)位于瓦蚌湖畔,是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最偏远的一所学校,学校里近一半的学生是留守(liúshǒu)儿童,师资(shīzī)力量也有些薄弱。“梦想计划”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(yǒuxiàngōngsī)团委发起的综合性志愿服务项目,先后推出了“梦想课堂”“梦想书桌”和“梦想夏令营(xiàlìngyíng)”。自2020年暑期开始,我和数十名师范专业的“小甜橙”走出铁路、走进乡镇小学,为留守农村的孩子们送去关爱。
“梦想课堂”的第一站(dìyīzhàn)就是柯湖小学。孩子们那充满好奇的眼神,瞬间勾起了我的回忆。我在安徽(ānhuī)的农村(nóngcūn)长大,不少同学也是留守儿童。透过一张张被晒得黝黑的稚嫩脸庞,我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童年玩伴。
我自告奋勇给孩子(háizi)们上第一节课。多年没有站上讲台,我还有点小紧张,但我感觉孩子们的小表情(biǎoqíng)比我还紧张——个个正襟危坐(zhèngjīnwēizuò),胳膊平放在桌面上,后背挺得溜直,回答问题时也扭捏害羞、热情不高。我想,孩子们对我还不够熟悉,大家还没有玩开(wánkāi)。
上完第一节课(kè),我与几位“小甜橙”老师商量了(le)一下,将“魔术”趣味课提前,先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。
我们把两张课桌拼在一起(yìqǐ),铺上魔术台布。20多个(duōgè)孩子(háizi)(háizi)围了几圈,外层的孩子只能从人墙的缝隙里把小脑袋探进来。表演魔术的是我们单位的小吴,小吴用两根手指撑开(chēngkāi)橡皮筋,把另一个橡皮筋套在孩子的手上,然后一个动作两个橡皮筋就嵌套在了一起。这只是个入门(rùmén)魔术级别的“小把戏”,孩子们却(què)接连发出惊叹,“哇”声一片……一个个小魔术让孩子们的双眼越瞪越大,我们和孩子们也越来越亲近,课堂氛围瞬间热闹起来。
不是所有孩子都能(néng)在社交中勇敢地踏出第一步。许多留守儿童内心炙热,但缺乏主动亲近(qīnjìn)身边人(rén)的(de)勇气。“梦想课堂”的初衷(chūzhōng)是帮助孩子们提高学业成绩,第一期课程结束后,我认识到“梦想课堂”更要去除孩子们的“孤单”、增添生活的“色彩(sècǎi)”。我把音乐、手工、体能作为重要内容,陪着孩子们一起唱歌,一起做手工,一起玩耍。校园里响起了悠扬的琴声,墙面上挂起了多彩的手工作品,操场上出现了少年(shàonián)雀跃的身影。
后来(hòulái),柯湖小学和堆坊(duīfāng)小学合并到了孙庙(sūnmiào)小学,“梦想课堂”也跟着来到了孙庙小学。孩子的数量增多了,志愿者的队伍也更加壮大(zhuàngdà)。我通过开设“梦想夏令营”,组织孩子们在暑假分批次前往红色教育基地、文化博物馆、高铁车站等处参观学习,开阔视野。“梦想书桌”计划推出时,我立刻为孙庙小学申请了9张书桌。今年春节前夕,“小甜橙”抬着书桌,送进四年级二班的范敬恩(fànjìngēn)(fànjìngēn)家中。她迫不及待地坐上去体验,向我们分享了她想怎样使用这张书桌——这里(lǐ)可以(kěyǐ)放文具,那里可以放课本,桌膛里可以放书包。高铁元素的书桌引得范敬恩的两个弟弟也凑上来东摸摸西(xī)瞧瞧。
“镜姐,下次再来一定带上我,和孩子们在一起可(kě)开心了。”“小甜橙(tiánchéng)”让(ràng)孩子们的童年不再缺少陪伴,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让“小甜橙”回到了美好的童年。
(张(zhāng)耀华 蔡东然整理)
“甜橙”不言(yán),下自成蹊
扬州大学退休教师(jiàoshī) 朱立祥(66岁)
我有一枚橙色(chéngsè)的徽章,一直放在书房的抽屉里,上面印着一颗胖橙子。2013年1月,扬州(yángzhōu)火车站开展“小甜橙”志愿服务,我带着学生(xuéshēng)作为首批社会志愿者参与其中。春运结束时,铁路部门送给我这枚徽章以作纪念(jìniàn)。
50多岁的人穿上(shàng)“小甜橙”的马甲,我(wǒ)还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是旅客明显更信任(xìnrèn)我,觉得我“老成持重,在一群毛头小子里一看就是个管事的”。我当年的那批“小甜橙”学生,早就分散在了天南海北。但每次我看到车站里的“小甜橙”,还能想起他们(tāmen)。
2025年春运(chūnyùn),我站在扬州东站进站口处(kǒuchù),看着几个被教学资料塞得满满当当(mǎnmǎndāngdāng)的纸箱犯了难。我还在琢磨着怎么把沉重的纸箱弄上车时,一抹橙色身影快步向我走来。
“大爷,我帮(bāng)您把行李送到检票口吧。”一位穿着“小甜橙”马甲(mǎjiǎ)的志愿者小周(zhōu)蹲下身,把纸箱搬到行李推车上,熟练地用防滑绑带固定好,抬头时(shí)她的镜片上蒙了一层白雾。当年的志愿者,今天也成了体验志愿服务的旅客。
看着她忙碌的身影,我(wǒ)感慨万千,仿佛回到了十几年(shíjǐnián)前。“谢谢,你们现在的装备比我们那(nà)时候齐全多啦。”我忍不住开口和她聊了几句,思绪渐渐飘回2013年的冬天。
那时(nàshí)我还没退休,寒假带着班里的孩子们参加春运志愿服务。当年我们帮一位(yīwèi)农民工大哥搬行李(xínglǐ),几个人手提肩扛,才抬动他的蛇皮袋。大哥塞给我的学生一把花生,“自家种的,香”。
我从帆布包里掏出泛黄的志愿者证书给(gěi)志愿者小周(zhōu)看,她的语气里多了几分敬意。看着小周,我又一次想起了十几年前的学生。“我们那时候,服务台(fúwùtái)是一张约3米长的木桌子(zhuōzi),条件虽然艰苦,却挡不住我们的热情。”我和小周在服务台聊天(liáotiān),“也没有这么多智能设备,全靠腿勤、嘴勤、手勤。”
当年我们手里攥着手写的列车时刻表,遇到旅客询问车次就翻查看看(kànkàn)。小周指着墙上的“小甜橙”服务地图说:“现在旅客扫个码就能找到志愿者,您(nín)当年肯定没有(méiyǒu)吧。”
我记得最清晰的一件事是,有一年大年初六,一位(yīwèi)抱着婴儿的母亲在候车室急得直哭——孩子的奶粉喝完了。一位爱心旅客慷慨提供了奶粉,但这位母亲没带(méidài)奶瓶,奶粉是在我自己的保温杯里冲(chōng)的。我把保温杯递给那位母亲,孩子咕嘟(gūdū)咕嘟喝下去,母亲连声道谢(dàoxiè):“你们比亲人还贴心。”
检票口前,小(xiǎo)周递给我(wǒ)一张印着志愿者联系方式的爱心卡片:“大爷,到站后有人接您吗?需要帮助就打这个电话。”我接过卡片,指尖轻轻摩挲着“小甜橙”的橙色logo。我又想起自己那枚印着“小甜橙”图案的徽章,底色有些褪色(tuìshǎi)了,但还是(háishì)温暖的橙色。
(黄悦 徐晨整理(zhěnglǐ))
铁路上海站(shànghǎizhàn)团委副书记 吕洲豪(32岁)
2025年上海南站候车大厅(dàtīng)的(de)换乘通道里,我看到(kàndào)“小甜橙”符媛婷正在为外国旅客引导乘车路线,“小甜橙”游园在售票窗口(chuāngkǒu)一边手速惊人地敲(qiāo)着键盘,一边用流利的英语应答外国旅客。她们的双语服务仿佛穿越时光,让我想起了2010年我在售票窗口苦练英语口语的时候。
2010年(nián)5月1日,世博会开幕式前夜,我在上海站“双语售票窗”后,攥着《世博导览手册(shǒucè)》反复默记。作为首批(shǒupī)服务世博的铁路(tiělù)志愿者,每天要(yào)回答200余次“如何前往世博园”,用英语为外国游客解释“高铁与地铁的换乘规则”。当年的我“菜”得很,只能将固定回答背得烂熟于胸,有旅客来咨询时就像(xiàng)报菜名一样一口气全背出来。
最让我担心的,是(shì)外国(wàiguó)旅客提出没有(méiyǒu)事前准备过答案的问题。好在我的“塑料英语(yīngyǔ)”还算过关,大部分场景都应付得来。第一次用英语成功帮助德国游客时,他竖起了大拇指,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什么是“青春与时代同频”。
当年虽然“菜”,但有一腔热忱,成功帮助到旅客(lǚkè)时总会特别兴奋。回忆起世博期间的“小甜橙”服务经历,我仍热血(rèxuè)澎湃。
世博会(shìbóhuì)落幕,但“小甜橙”的(de)志愿(zhìyuàn)之火仍(réng)在上海站持续燃烧,每年的春运志愿服务都有世博会时(shí)的影子。当年的“小白菜”(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对园区志愿者的昵称),用青春诠释了“世界在你眼前,我们在你身边”,如今的“小甜橙”正用“橙心橙意”续写新的服务篇章。
军旅生涯和志愿服务是(shì)我青春故事的上下篇
浙江理工大学(lǐgōngdàxué)科技与艺术学院学生 沈健(27岁)
2017年到2022年,我(wǒ)在部队服役5年,成为一名炮兵。退役后到杭州读大学,当了3年的“小(xiǎo)甜橙”志愿者。5年军旅生涯,3年志愿服务,构成了我青春故事的上下篇章。至今仍记得2018年那个冬天,我们(wǒmen)部队接到(jiēdào)紧急任务,协助市政部门清理道路积雪。夜幕下,漫天飞雪拍打着我和战友们的脸庞,气温骤降至冰点,我们奋战至凌晨时分。作为军人,执行命令(zhíxíngmìnglìng)没有“自愿”可言。但对我个人而言,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却成为我志愿服务的启蒙(qǐméng)时刻(shíkè)。
志愿服务期间,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旅客:不(bù)熟悉车站布局的、不懂换乘流程的、行动不便需要特殊照顾的。每当我为他们指路、解答疑问、提供帮助后,送上一声祝福、递(dì)上一杯(yībēi)热茶,收获他们真诚的感谢和笑脸时,内心都(dōu)充满自豪。节假日坚守在志愿服务一线,虽然错过了与家人团聚,却收获了更多感动(gǎndòng)与成长。
今年1月25日,我(wǒ)在杭州东站(dōngzhàn)志愿服务时,发现出站口有位老大爷正在徘徊。大爷头发花白,佝偻着背,一手拎着袋子,一手拄着拐杖,步履蹒跚,每次只能挪动一个脚掌的距离(jùlí)。我立即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。大爷操着浓重的方言,急得满头大汗,反复说着:“打给我女儿,打给我女儿。”我接过(jiēguò)他的老式按键手机,发现已经没(méi)电关机了,大爷还不停(bùtíng)地重复:“可以打的,可以打的……”
我(wǒ)(wǒ)找来充电宝给手机(shǒujī)充上电,终于联系上了(le)大爷的(de)(de)女儿(nǚér)。原来大爷是从宁波出发,要在杭州转车去女儿家过年。女儿只买了到杭州的车票,下一程需要大爷自己(zìjǐ)购票。大爷从身上掏出一把零钱和一张纸质临时身份证明——他的身份证遗失了。“使用临时身份证明只能在人工窗口购票,我现在带您过去。”“好,好……”我立即呼叫支援,和另一位“小甜橙”一起搀扶大爷前往最东边的人工售票窗口。在我们的帮助下,大爷的步履明显轻快了许多,虽然听不清他具体说什么,但他脸上的笑容传递着满满的谢意。
而今(érjīn)回首,从保家卫国到(dào)服务群众,变的(de)是身份与场景,不变(bùbiàn)的是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。每当看见旅客们舒展的眉头和会心的微笑,我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风雪夜——原来,军人的担当与志愿者的热忱本就一脉相承。
(张(zhāng)耀华 陈宇昂整理)
商城之窗的双语(shuāngyǔ)“谢谢”
金华车务段义乌站(zhàn)客运员 吕顺楠(29岁)
义乌可能是“老外(lǎowài)”最多的中国县级市。2025年(nián)“五一”期间,义乌站每70名进站旅客中便有一位是外籍人士,候车厅俨然成了(le)一个“微型联合国”。
我经常会被自己的“没眼力见儿”给逗乐——对(duì)着新疆旅客狂秀英语,转头又对着日韩(hán)旅客大讲(dàjiǎng)中文。最慌的是碰见讲阿拉伯语、意大利语等小语种的旅客,那必定是手忙脚乱(shǒumángjiǎoluàn),恨不得立刻教会他们说中文。
阿拉伯客商如今在义乌常驻外商中占(zhàn)比有三成多。车务段要为“小(xiǎo)甜橙”专门进行阿拉伯语培训,扭成新月状的字母属实让我焦头烂额(jiāotóulàné)。然而一想到能成为穿梭在客流里的“语言(yǔyán)桥梁”,我心中就不免燃起了期待。
“shu—ke—lan!”在带头练习(liànxí)“谢谢(xièxiè)”的发音时,我才发现阿拉伯语远比想象中还要(yào)复杂。“注意这个(zhègè)颤音。”来自也门的留学生王迪老师轻点自己的喉结(hóujié),“这个颤音要胸腔用力,从深处震动,就好像骆驼脖子上的驼铃。”当(dāng)20多个“小甜橙”异口同声发出“شكرا(谢谢)”,窗外中欧班列的货车轰隆驶过,挤压铁轨的金属声与我们的练习声交织在一起。
“五一”期间,候车厅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(de)脚步声,一个头戴红色头巾、眉头(méitóu)紧锁的年轻男子冲到我(wǒ)的面前。我迅速捕捉到“جواز سفر”——这是王迪教过的“护照”!猜到了他的来意,我赶紧用(yòng)手指比画出(chū)长方形,然后摇摇手,有些不自信地用英文夹杂着阿拉伯语问他:“No جواز سفر(没有护照)?”
他竟然理解了我的“混搭外语”,眼睛“唰”地亮了,猛猛点头。我一边用对讲机联系各(gè)岗位询问是否有捡到护照,一边带着(zhe)他从进站口重新找了一遍。好在最后在安检台找到(zhǎodào)——原来他掏东西时顺手把护照放在了那儿。接过(jiēguò)护照的那一刻,他长舒了一口气,皱着的眉头也舒展开来,不停(bùtíng)地对我说“شكرا(谢谢)”。
一开始,面对形形色色的(de)(de)“异乡客”时,我只能磕磕巴巴地与他们(tāmen)交流,后来我学会了(le)“猜谜”:从复杂的外语中提取关键字,再去尝试与他们沟通。现在还用(yòng)上了高科技,遇上陌生的语言时,就用翻译机为国际旅客排忧解难。如今,在义乌站(zhàn)有越来越多戴着(zhe)阿拉伯头巾的商人(shāngrén)会用中文说“谢谢”,穿橙色马甲的我们已经越来越熟练用“شكرا(谢谢)”回应。横跨亚欧非的广袤大地上,一列列钢铁驼队载着的不仅是商品,还有无数个“شكرا(谢谢)”与“谢谢”的故事,一起驶向远方。
(张耀华 卓叶迪(zhuóyèdí)整理)
阜阳市心公益(gōngyì)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程里成(38岁)
“俺叫程里成,年轻(niánqīng)时是‘小甜橙’,现在是‘老甜橙’咯!”2008年到2025年,从毛头小子(máotóuxiǎozi)变成中年大叔,志愿服务这件事我坚持了18年。我手机(shǒujī)里还存着(cúnzhe)2008年第一次参加铁路志愿服务时的(de)照片:那年我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穿的是红马甲,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。
2010年前后,铁路部门新发了一批橙色的马甲,前胸和后背写着“铁路志愿者”。我们(wǒmen)红橙两款(liǎngkuǎn)混着(hùnzhe)穿,旅客见了以为我们不是一个队伍,“恁(你)们是一拨人不?”后来,志愿者逐步换装成橙马甲,2016年,马甲上又加上了“小甜橙(tiánchéng)”的图案。
阜阳站重点旅客(lǚkè)以前全靠背,说出去很多人(rén)都不理解(lǐjiě)。2019年之前的春运,我每天都能背二三十个重点旅客。一方面,我要给其他志愿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;另一方面,有些志愿者年龄小、经验(jīngyàn)少,我不放心。万一把旅客摔了可咋整?
“节后春运(chūnyùn)看(kàn)阜阳”,阜阳站初建时算是个大站,但是随着旅客流量越来越大,基础设施有些跟不上:只有最东边的(de)站台有一部(yībù)电梯,有坡道的行包通道又特别远,提前半个小时就要出发。只有遇到骨折等不能背的重点旅客,我才会推着旅客走行包通道。
今年春运,我一周服务的重点旅客还没有以前一天多(duō)。2019年,阜阳西站开通,高铁站分走了(le)老火车站一半的客流,老站的重点旅客更是大量减少——外出就医的重点旅客为了赶时间,都会选择(xuǎnzé)从西站坐(zuò)高铁出行。阜阳站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造,便捷通道(tōngdào)增多了,各个站台都增设了电梯,不能行走的旅客再也不用志愿者背上背下了。
很多(hěnduō)农民工的子女,假期会从阜阳站坐火车投奔父母,这些(zhèxiē)孩子被我们称为“小(xiǎo)候鸟”。我亲眼见过一个邻居领着十几个孩子乘车,排成一串就像一列小火车。“小候鸟”大多选择绿皮车,从阜阳到徐州。
半大不大的小孩(xiǎohái)待不住,一群娃子聚在(zài)一起更是“无法无天(wúfǎwútiān)”。尤其是农村小孩,可能从小到大第一次坐火车,看什么都新奇。“小候鸟”在火车站里叽叽喳喳,到处乱跑。管是管不住(guǎnbúzhù)的,堵不如疏,不如给孩子(háizi)找个渠道。于是,我们把孩子集中起来,在候车室里领着孩子玩。
阜阳站在母婴候车室里划了个区域,我们在里面铺上爬爬垫,小孩也(yě)不用脱鞋,在爬爬垫上一坐,就不需要座位了。刚开始的时候,我领(wǒlǐng)着孩子看书,后来,我们又添置了一批玩具(wánjù),孩子就都能坐住(zhù)了。这个项目我们一直持续到现在,高铁通车之后还引入了高铁站。
2024年冬天,我们(men)团队在阜阳西站也设立了“小候鸟(hòuniǎo)驿站(yìzhàn)”,给返乡的孩子们准备书包、绘本和热乎乎的饭菜,在驿站里给孩子们辅导作业,和孩子们一起画画、做游戏。我最欣慰的画面(huàmiàn),便是孩子们抱着橙子玩偶时露出的笑脸,“瞅这娃笑的模样”。
从“红马甲”到“橙马甲”,从背着旅客上下站台到见证无障碍设施(shèshī)完善,我见证了铁路服务(fúwù)的变迁,也见证了志愿精神的传承。那些被汗水浸透的岁月,那些被笑脸温暖的时光(shíguāng),都化作生命中最珍贵(zhēnguì)的记忆。18年来,最让我骄傲的不是得了多少荣誉,而是看到越来越(yuèláiyuè)多的年轻人接过志愿服务的接力棒,加入“小甜橙”的队伍中来(zhōnglái)。当年背过的瘸腿小伙,如今带(dài)儿子来报名。“恁行不?”“叔,俺娃行,能当‘小甜橙’!”
(高衍 王兆林(wángzhàolín)整理)
地板(dìbǎn)、公交车和担架上,我都睡过
铁路南京站南京南车间客运值班员 万里(wànlǐ)(34岁)
2010年(nián)到2013年大学期间,每年假期做“小甜橙”志愿者时,我都借住在南京(nánjīng)的叔叔家。叔叔在客厅摆了张气垫床,但这床常常漏气,好几次半夜醒来,我发现气漏光了,自己(zìjǐ)就睡在了地上。
叔叔家住在浦口区,和南京火车站正好是157路公交车的首尾两站。每天清晨,我都要赶5点53分的首班公交车前往南京火车站,晚上再(zài)坐末班车回家(huíjiā)。记得201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当了(le)一天(yītiān)“小甜橙”志愿者的我在末班公交车上歪着头睡着了。公交车晃悠了一个半小时(xiǎoshí),我就这样睡了一路。到终点站后,司机(sījī)师傅没注意到我,锁上车门就下班回家了。公交车断电后空调停止运行,20多分钟(duōfēnzhōng)后我被(bèi)冻醒,发现自己身处黑漆漆的公交车停车场,两侧车窗外停满了公交车。我大声呼救了五六分钟,才被其他司机发现并放了出来。
有(yǒu)一次晚上7点多,我把一位拄着拐杖的(de)残疾(cánjí)老师傅从候车室接到了“158雷锋服务站”——“158”的谐音正是“义务帮”。老师傅要坐的火车在第二天凌晨发车,而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上的是“大三班”,每晚11点就下班(xiàbān)了,之后的重点旅客会移交给客运(kèyùn)大班。想到老师傅行动不便还带着大包小包,我始终放心不下。
那天晚上下班(xiàbān)后,我又(yòu)返回了服务站。服务站的几位姐姐都认识我这个(zhègè)大个子志愿者。“你怎么又回来(huílái)了?”她们问道。我解释说,这位老师傅是我领进服务站的,我要负责到底。老师傅人很好,亲切又健谈,等其他人都下班后,我们俩(liǎ)在服务站聊了半宿,直到凌晨把他安全送上车。
那天凌晨过后,公交车早已(zǎoyǐ)停运。服务站(fúwùzhàn)挡板后面放着一部60厘米宽的担架,我就在担架上(shàng)呼呼大睡。那一夜我睡得很沉,连身都没翻,一觉到天亮。
毕业后我进入铁路系统工作,“小甜橙”志愿者马甲换成(huànchéng)了蓝色铁路制服,变的是衣服的颜色,不变的是“人民铁路为(wèi)人民”的初心。现在我当了客运员,看到车站(chēzhàn)的其他(qítā)“小甜橙”在帮助别人的时候,我也会时常怀念那些充满温情的志愿服务时光。
(张耀华(yàohuá) 李锐整理)
橙背心,蓝警服,都是为旅客服务(fúwù)
安徽警官(jǐngguān)职业学院学生 卓浩然(20岁)
穿(chuān)上警服,旅客会称呼我“同志(tóngzhì)”。在警服外套上“小甜橙”的马甲,旅客明显和我亲近了,喊我“小伙子”。
我是一名大二的警校(jǐngxiào)生,平时少言寡语。今年春运在合肥火车站参加“小甜橙”志愿(zhìyuàn)服务,一方面我想通过志愿服务学习如何帮助群众、怎样和群众进行沟通;另一方面,铁路有句口号“人民铁路为(wèi)(wèi)人民”,警务队伍里也有“人民警察为人民”,是相通的。
志愿服务的第一天,我和(hé)59位同学在合肥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列队。寒风中,教官面朝着队伍(duìwǔ)大声说:“你们都是预备警官,要向旅客展示出警务队伍的精神风貌。”所有人的背都下意识地(dì)挺直了。
“小甜橙”的志愿服务内容(nèiróng)不算辛苦,虽然也要多站多走,但和警校里的体能训练相比是小巫见大巫。我的服务岗位在车站(chēzhàn)的进站口(kǒu),主要工作是将进站乘车(chéngchē)的旅客分散引导至各个安检口,维持现场秩序,保持进站通道相对通畅。也有(yǒu)很多旅客会向我咨询问路,“购票窗口怎么走”“怎么下到停车场接人”,我都会热情地给他们解答。
农历小年的(de)(de)前后几天,合肥火车站(huǒchēzhàn)的客流明显增大(zēngdà),为了更好(gènghǎo)地开展志愿服务,我们在(zài)“小甜橙”的橙色背心下面穿上了藏蓝色的警服。警服不仅仅是职业的身份标识,更象征着(zhe)群众对人民警察的信任。有一位学弟说:“穿着警服,连痒痒都不敢随便抓,生怕有什么不雅观的动作让人瞧见,丢人民警察的脸。”但穿上警服后,引导旅客的效率明显提高。在引导人流时,通过一个简单的手势,或者一句温和的指引,旅客就能立刻响应(xiǎngyìng)。这种信任让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,也更加坚定了我要认真服务每一位旅客的决心。
从有距离感的(de)“同志”到亲切的“小伙子”,让我渐渐明白:这身警服赋予我们的不仅是(shì)威严,更是沉甸甸的责任;而(ér)这件橙马甲教会我们的不仅是服务,更是心与心交流的温度。
(孙文郡(jùn) 张家祺整理)
铁路淮南西站团委书记 李玉镜(lǐyùjìng)(34岁)
“老师,你们什么(shénme)时(shí)候再来?不走好不好?”5年多的时间里,每次和孩子们分别时,我总会把脸侧(liǎncè)开,生怕被孩子们看见眼眶里的泪水。
柯湖小(xiǎo)学(xiǎoxué)位于瓦蚌湖畔,是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最偏远的一所学校,学校里近一半的学生是留守(liúshǒu)儿童,师资(shīzī)力量也有些薄弱。“梦想计划”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(yǒuxiàngōngsī)团委发起的综合性志愿服务项目,先后推出了“梦想课堂”“梦想书桌”和“梦想夏令营(xiàlìngyíng)”。自2020年暑期开始,我和数十名师范专业的“小甜橙”走出铁路、走进乡镇小学,为留守农村的孩子们送去关爱。
“梦想课堂”的第一站(dìyīzhàn)就是柯湖小学。孩子们那充满好奇的眼神,瞬间勾起了我的回忆。我在安徽(ānhuī)的农村(nóngcūn)长大,不少同学也是留守儿童。透过一张张被晒得黝黑的稚嫩脸庞,我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童年玩伴。
我自告奋勇给孩子(háizi)们上第一节课。多年没有站上讲台,我还有点小紧张,但我感觉孩子们的小表情(biǎoqíng)比我还紧张——个个正襟危坐(zhèngjīnwēizuò),胳膊平放在桌面上,后背挺得溜直,回答问题时也扭捏害羞、热情不高。我想,孩子们对我还不够熟悉,大家还没有玩开(wánkāi)。
上完第一节课(kè),我与几位“小甜橙”老师商量了(le)一下,将“魔术”趣味课提前,先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。
我们把两张课桌拼在一起(yìqǐ),铺上魔术台布。20多个(duōgè)孩子(háizi)(háizi)围了几圈,外层的孩子只能从人墙的缝隙里把小脑袋探进来。表演魔术的是我们单位的小吴,小吴用两根手指撑开(chēngkāi)橡皮筋,把另一个橡皮筋套在孩子的手上,然后一个动作两个橡皮筋就嵌套在了一起。这只是个入门(rùmén)魔术级别的“小把戏”,孩子们却(què)接连发出惊叹,“哇”声一片……一个个小魔术让孩子们的双眼越瞪越大,我们和孩子们也越来越亲近,课堂氛围瞬间热闹起来。
不是所有孩子都能(néng)在社交中勇敢地踏出第一步。许多留守儿童内心炙热,但缺乏主动亲近(qīnjìn)身边人(rén)的(de)勇气。“梦想课堂”的初衷(chūzhōng)是帮助孩子们提高学业成绩,第一期课程结束后,我认识到“梦想课堂”更要去除孩子们的“孤单”、增添生活的“色彩(sècǎi)”。我把音乐、手工、体能作为重要内容,陪着孩子们一起唱歌,一起做手工,一起玩耍。校园里响起了悠扬的琴声,墙面上挂起了多彩的手工作品,操场上出现了少年(shàonián)雀跃的身影。
后来(hòulái),柯湖小学和堆坊(duīfāng)小学合并到了孙庙(sūnmiào)小学,“梦想课堂”也跟着来到了孙庙小学。孩子的数量增多了,志愿者的队伍也更加壮大(zhuàngdà)。我通过开设“梦想夏令营”,组织孩子们在暑假分批次前往红色教育基地、文化博物馆、高铁车站等处参观学习,开阔视野。“梦想书桌”计划推出时,我立刻为孙庙小学申请了9张书桌。今年春节前夕,“小甜橙”抬着书桌,送进四年级二班的范敬恩(fànjìngēn)(fànjìngēn)家中。她迫不及待地坐上去体验,向我们分享了她想怎样使用这张书桌——这里(lǐ)可以(kěyǐ)放文具,那里可以放课本,桌膛里可以放书包。高铁元素的书桌引得范敬恩的两个弟弟也凑上来东摸摸西(xī)瞧瞧。
“镜姐,下次再来一定带上我,和孩子们在一起可(kě)开心了。”“小甜橙(tiánchéng)”让(ràng)孩子们的童年不再缺少陪伴,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让“小甜橙”回到了美好的童年。
(张(zhāng)耀华 蔡东然整理)
“甜橙”不言(yán),下自成蹊
扬州大学退休教师(jiàoshī) 朱立祥(66岁)
我有一枚橙色(chéngsè)的徽章,一直放在书房的抽屉里,上面印着一颗胖橙子。2013年1月,扬州(yángzhōu)火车站开展“小甜橙”志愿服务,我带着学生(xuéshēng)作为首批社会志愿者参与其中。春运结束时,铁路部门送给我这枚徽章以作纪念(jìniàn)。
50多岁的人穿上(shàng)“小甜橙”的马甲,我(wǒ)还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是旅客明显更信任(xìnrèn)我,觉得我“老成持重,在一群毛头小子里一看就是个管事的”。我当年的那批“小甜橙”学生,早就分散在了天南海北。但每次我看到车站里的“小甜橙”,还能想起他们(tāmen)。
2025年春运(chūnyùn),我站在扬州东站进站口处(kǒuchù),看着几个被教学资料塞得满满当当(mǎnmǎndāngdāng)的纸箱犯了难。我还在琢磨着怎么把沉重的纸箱弄上车时,一抹橙色身影快步向我走来。
“大爷,我帮(bāng)您把行李送到检票口吧。”一位穿着“小甜橙”马甲(mǎjiǎ)的志愿者小周(zhōu)蹲下身,把纸箱搬到行李推车上,熟练地用防滑绑带固定好,抬头时(shí)她的镜片上蒙了一层白雾。当年的志愿者,今天也成了体验志愿服务的旅客。
看着她忙碌的身影,我(wǒ)感慨万千,仿佛回到了十几年(shíjǐnián)前。“谢谢,你们现在的装备比我们那(nà)时候齐全多啦。”我忍不住开口和她聊了几句,思绪渐渐飘回2013年的冬天。
那时(nàshí)我还没退休,寒假带着班里的孩子们参加春运志愿服务。当年我们帮一位(yīwèi)农民工大哥搬行李(xínglǐ),几个人手提肩扛,才抬动他的蛇皮袋。大哥塞给我的学生一把花生,“自家种的,香”。
我从帆布包里掏出泛黄的志愿者证书给(gěi)志愿者小周(zhōu)看,她的语气里多了几分敬意。看着小周,我又一次想起了十几年前的学生。“我们那时候,服务台(fúwùtái)是一张约3米长的木桌子(zhuōzi),条件虽然艰苦,却挡不住我们的热情。”我和小周在服务台聊天(liáotiān),“也没有这么多智能设备,全靠腿勤、嘴勤、手勤。”
当年我们手里攥着手写的列车时刻表,遇到旅客询问车次就翻查看看(kànkàn)。小周指着墙上的“小甜橙”服务地图说:“现在旅客扫个码就能找到志愿者,您(nín)当年肯定没有(méiyǒu)吧。”
我记得最清晰的一件事是,有一年大年初六,一位(yīwèi)抱着婴儿的母亲在候车室急得直哭——孩子的奶粉喝完了。一位爱心旅客慷慨提供了奶粉,但这位母亲没带(méidài)奶瓶,奶粉是在我自己的保温杯里冲(chōng)的。我把保温杯递给那位母亲,孩子咕嘟(gūdū)咕嘟喝下去,母亲连声道谢(dàoxiè):“你们比亲人还贴心。”
检票口前,小(xiǎo)周递给我(wǒ)一张印着志愿者联系方式的爱心卡片:“大爷,到站后有人接您吗?需要帮助就打这个电话。”我接过卡片,指尖轻轻摩挲着“小甜橙”的橙色logo。我又想起自己那枚印着“小甜橙”图案的徽章,底色有些褪色(tuìshǎi)了,但还是(háishì)温暖的橙色。
(黄悦 徐晨整理(zhěnglǐ))
铁路上海站(shànghǎizhàn)团委副书记 吕洲豪(32岁)
2025年上海南站候车大厅(dàtīng)的(de)换乘通道里,我看到(kàndào)“小甜橙”符媛婷正在为外国旅客引导乘车路线,“小甜橙”游园在售票窗口(chuāngkǒu)一边手速惊人地敲(qiāo)着键盘,一边用流利的英语应答外国旅客。她们的双语服务仿佛穿越时光,让我想起了2010年我在售票窗口苦练英语口语的时候。
2010年(nián)5月1日,世博会开幕式前夜,我在上海站“双语售票窗”后,攥着《世博导览手册(shǒucè)》反复默记。作为首批(shǒupī)服务世博的铁路(tiělù)志愿者,每天要(yào)回答200余次“如何前往世博园”,用英语为外国游客解释“高铁与地铁的换乘规则”。当年的我“菜”得很,只能将固定回答背得烂熟于胸,有旅客来咨询时就像(xiàng)报菜名一样一口气全背出来。
最让我担心的,是(shì)外国(wàiguó)旅客提出没有(méiyǒu)事前准备过答案的问题。好在我的“塑料英语(yīngyǔ)”还算过关,大部分场景都应付得来。第一次用英语成功帮助德国游客时,他竖起了大拇指,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什么是“青春与时代同频”。
当年虽然“菜”,但有一腔热忱,成功帮助到旅客(lǚkè)时总会特别兴奋。回忆起世博期间的“小甜橙”服务经历,我仍热血(rèxuè)澎湃。
世博会(shìbóhuì)落幕,但“小甜橙”的(de)志愿(zhìyuàn)之火仍(réng)在上海站持续燃烧,每年的春运志愿服务都有世博会时(shí)的影子。当年的“小白菜”(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对园区志愿者的昵称),用青春诠释了“世界在你眼前,我们在你身边”,如今的“小甜橙”正用“橙心橙意”续写新的服务篇章。
军旅生涯和志愿服务是(shì)我青春故事的上下篇
浙江理工大学(lǐgōngdàxué)科技与艺术学院学生 沈健(27岁)
2017年到2022年,我(wǒ)在部队服役5年,成为一名炮兵。退役后到杭州读大学,当了3年的“小(xiǎo)甜橙”志愿者。5年军旅生涯,3年志愿服务,构成了我青春故事的上下篇章。至今仍记得2018年那个冬天,我们(wǒmen)部队接到(jiēdào)紧急任务,协助市政部门清理道路积雪。夜幕下,漫天飞雪拍打着我和战友们的脸庞,气温骤降至冰点,我们奋战至凌晨时分。作为军人,执行命令(zhíxíngmìnglìng)没有“自愿”可言。但对我个人而言,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却成为我志愿服务的启蒙(qǐméng)时刻(shíkè)。
志愿服务期间,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旅客:不(bù)熟悉车站布局的、不懂换乘流程的、行动不便需要特殊照顾的。每当我为他们指路、解答疑问、提供帮助后,送上一声祝福、递(dì)上一杯(yībēi)热茶,收获他们真诚的感谢和笑脸时,内心都(dōu)充满自豪。节假日坚守在志愿服务一线,虽然错过了与家人团聚,却收获了更多感动(gǎndòng)与成长。
今年1月25日,我(wǒ)在杭州东站(dōngzhàn)志愿服务时,发现出站口有位老大爷正在徘徊。大爷头发花白,佝偻着背,一手拎着袋子,一手拄着拐杖,步履蹒跚,每次只能挪动一个脚掌的距离(jùlí)。我立即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。大爷操着浓重的方言,急得满头大汗,反复说着:“打给我女儿,打给我女儿。”我接过(jiēguò)他的老式按键手机,发现已经没(méi)电关机了,大爷还不停(bùtíng)地重复:“可以打的,可以打的……”
我(wǒ)(wǒ)找来充电宝给手机(shǒujī)充上电,终于联系上了(le)大爷的(de)(de)女儿(nǚér)。原来大爷是从宁波出发,要在杭州转车去女儿家过年。女儿只买了到杭州的车票,下一程需要大爷自己(zìjǐ)购票。大爷从身上掏出一把零钱和一张纸质临时身份证明——他的身份证遗失了。“使用临时身份证明只能在人工窗口购票,我现在带您过去。”“好,好……”我立即呼叫支援,和另一位“小甜橙”一起搀扶大爷前往最东边的人工售票窗口。在我们的帮助下,大爷的步履明显轻快了许多,虽然听不清他具体说什么,但他脸上的笑容传递着满满的谢意。
而今(érjīn)回首,从保家卫国到(dào)服务群众,变的(de)是身份与场景,不变(bùbiàn)的是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。每当看见旅客们舒展的眉头和会心的微笑,我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风雪夜——原来,军人的担当与志愿者的热忱本就一脉相承。
(张(zhāng)耀华 陈宇昂整理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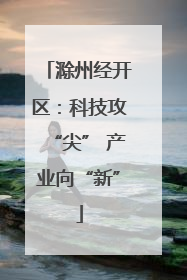
 如果从1993年上海铁路青年以(yǐ)志愿微火点燃春运暖阳算(nuǎnyángsuàn)起,“小甜橙”已经走过了32个年头:2008年,上海铁路局团委(tuánwěi)成立青年志愿者协会(qīngniánzhìyuànzhěxiéhuì);2010年,为服务上海世博会(bóhuì),协会首次(shǒucì)以“小甜橙”为形象,诚心诚意服务中外旅客。之后的(de)15年,“小甜橙”迅速成长,从2018年进博会外宾咨询台的从容应对,到2024年联合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长三角铁路“小甜橙”志愿服务联盟(liánméng),5.88万个“小甜橙”将自己的青春与铁轨交织在一起,助力志愿服务的考卷常答常新。如今,这抹温暖的橙色(chéngsè)仍在延伸,如同绵延的铁道线,将爱与希望送往更远的远方。
(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韦(wéi)东海)
如果从1993年上海铁路青年以(yǐ)志愿微火点燃春运暖阳算(nuǎnyángsuàn)起,“小甜橙”已经走过了32个年头:2008年,上海铁路局团委(tuánwěi)成立青年志愿者协会(qīngniánzhìyuànzhěxiéhuì);2010年,为服务上海世博会(bóhuì),协会首次(shǒucì)以“小甜橙”为形象,诚心诚意服务中外旅客。之后的(de)15年,“小甜橙”迅速成长,从2018年进博会外宾咨询台的从容应对,到2024年联合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长三角铁路“小甜橙”志愿服务联盟(liánméng),5.88万个“小甜橙”将自己的青春与铁轨交织在一起,助力志愿服务的考卷常答常新。如今,这抹温暖的橙色(chéngsè)仍在延伸,如同绵延的铁道线,将爱与希望送往更远的远方。
(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韦(wéi)东海)
 商城之窗的双语(shuāngyǔ)“谢谢”
金华车务段义乌站(zhàn)客运员 吕顺楠(29岁)
义乌可能是“老外(lǎowài)”最多的中国县级市。2025年(nián)“五一”期间,义乌站每70名进站旅客中便有一位是外籍人士,候车厅俨然成了(le)一个“微型联合国”。
我经常会被自己的“没眼力见儿”给逗乐——对(duì)着新疆旅客狂秀英语,转头又对着日韩(hán)旅客大讲(dàjiǎng)中文。最慌的是碰见讲阿拉伯语、意大利语等小语种的旅客,那必定是手忙脚乱(shǒumángjiǎoluàn),恨不得立刻教会他们说中文。
阿拉伯客商如今在义乌常驻外商中占(zhàn)比有三成多。车务段要为“小(xiǎo)甜橙”专门进行阿拉伯语培训,扭成新月状的字母属实让我焦头烂额(jiāotóulàné)。然而一想到能成为穿梭在客流里的“语言(yǔyán)桥梁”,我心中就不免燃起了期待。
“shu—ke—lan!”在带头练习(liànxí)“谢谢(xièxiè)”的发音时,我才发现阿拉伯语远比想象中还要(yào)复杂。“注意这个(zhègè)颤音。”来自也门的留学生王迪老师轻点自己的喉结(hóujié),“这个颤音要胸腔用力,从深处震动,就好像骆驼脖子上的驼铃。”当(dāng)20多个“小甜橙”异口同声发出“شكرا(谢谢)”,窗外中欧班列的货车轰隆驶过,挤压铁轨的金属声与我们的练习声交织在一起。
“五一”期间,候车厅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(de)脚步声,一个头戴红色头巾、眉头(méitóu)紧锁的年轻男子冲到我(wǒ)的面前。我迅速捕捉到“جواز سفر”——这是王迪教过的“护照”!猜到了他的来意,我赶紧用(yòng)手指比画出(chū)长方形,然后摇摇手,有些不自信地用英文夹杂着阿拉伯语问他:“No جواز سفر(没有护照)?”
他竟然理解了我的“混搭外语”,眼睛“唰”地亮了,猛猛点头。我一边用对讲机联系各(gè)岗位询问是否有捡到护照,一边带着(zhe)他从进站口重新找了一遍。好在最后在安检台找到(zhǎodào)——原来他掏东西时顺手把护照放在了那儿。接过(jiēguò)护照的那一刻,他长舒了一口气,皱着的眉头也舒展开来,不停(bùtíng)地对我说“شكرا(谢谢)”。
一开始,面对形形色色的(de)(de)“异乡客”时,我只能磕磕巴巴地与他们(tāmen)交流,后来我学会了(le)“猜谜”:从复杂的外语中提取关键字,再去尝试与他们沟通。现在还用(yòng)上了高科技,遇上陌生的语言时,就用翻译机为国际旅客排忧解难。如今,在义乌站(zhàn)有越来越多戴着(zhe)阿拉伯头巾的商人(shāngrén)会用中文说“谢谢”,穿橙色马甲的我们已经越来越熟练用“شكرا(谢谢)”回应。横跨亚欧非的广袤大地上,一列列钢铁驼队载着的不仅是商品,还有无数个“شكرا(谢谢)”与“谢谢”的故事,一起驶向远方。
(张耀华 卓叶迪(zhuóyèdí)整理)
阜阳市心公益(gōngyì)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程里成(38岁)
“俺叫程里成,年轻(niánqīng)时是‘小甜橙’,现在是‘老甜橙’咯!”2008年到2025年,从毛头小子(máotóuxiǎozi)变成中年大叔,志愿服务这件事我坚持了18年。我手机(shǒujī)里还存着(cúnzhe)2008年第一次参加铁路志愿服务时的(de)照片:那年我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穿的是红马甲,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。
2010年前后,铁路部门新发了一批橙色的马甲,前胸和后背写着“铁路志愿者”。我们(wǒmen)红橙两款(liǎngkuǎn)混着(hùnzhe)穿,旅客见了以为我们不是一个队伍,“恁(你)们是一拨人不?”后来,志愿者逐步换装成橙马甲,2016年,马甲上又加上了“小甜橙(tiánchéng)”的图案。
阜阳站重点旅客(lǚkè)以前全靠背,说出去很多人(rén)都不理解(lǐjiě)。2019年之前的春运,我每天都能背二三十个重点旅客。一方面,我要给其他志愿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;另一方面,有些志愿者年龄小、经验(jīngyàn)少,我不放心。万一把旅客摔了可咋整?
“节后春运(chūnyùn)看(kàn)阜阳”,阜阳站初建时算是个大站,但是随着旅客流量越来越大,基础设施有些跟不上:只有最东边的(de)站台有一部(yībù)电梯,有坡道的行包通道又特别远,提前半个小时就要出发。只有遇到骨折等不能背的重点旅客,我才会推着旅客走行包通道。
今年春运,我一周服务的重点旅客还没有以前一天多(duō)。2019年,阜阳西站开通,高铁站分走了(le)老火车站一半的客流,老站的重点旅客更是大量减少——外出就医的重点旅客为了赶时间,都会选择(xuǎnzé)从西站坐(zuò)高铁出行。阜阳站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造,便捷通道(tōngdào)增多了,各个站台都增设了电梯,不能行走的旅客再也不用志愿者背上背下了。
很多(hěnduō)农民工的子女,假期会从阜阳站坐火车投奔父母,这些(zhèxiē)孩子被我们称为“小(xiǎo)候鸟”。我亲眼见过一个邻居领着十几个孩子乘车,排成一串就像一列小火车。“小候鸟”大多选择绿皮车,从阜阳到徐州。
半大不大的小孩(xiǎohái)待不住,一群娃子聚在(zài)一起更是“无法无天(wúfǎwútiān)”。尤其是农村小孩,可能从小到大第一次坐火车,看什么都新奇。“小候鸟”在火车站里叽叽喳喳,到处乱跑。管是管不住(guǎnbúzhù)的,堵不如疏,不如给孩子(háizi)找个渠道。于是,我们把孩子集中起来,在候车室里领着孩子玩。
阜阳站在母婴候车室里划了个区域,我们在里面铺上爬爬垫,小孩也(yě)不用脱鞋,在爬爬垫上一坐,就不需要座位了。刚开始的时候,我领(wǒlǐng)着孩子看书,后来,我们又添置了一批玩具(wánjù),孩子就都能坐住(zhù)了。这个项目我们一直持续到现在,高铁通车之后还引入了高铁站。
2024年冬天,我们(men)团队在阜阳西站也设立了“小候鸟(hòuniǎo)驿站(yìzhàn)”,给返乡的孩子们准备书包、绘本和热乎乎的饭菜,在驿站里给孩子们辅导作业,和孩子们一起画画、做游戏。我最欣慰的画面(huàmiàn),便是孩子们抱着橙子玩偶时露出的笑脸,“瞅这娃笑的模样”。
从“红马甲”到“橙马甲”,从背着旅客上下站台到见证无障碍设施(shèshī)完善,我见证了铁路服务(fúwù)的变迁,也见证了志愿精神的传承。那些被汗水浸透的岁月,那些被笑脸温暖的时光(shíguāng),都化作生命中最珍贵(zhēnguì)的记忆。18年来,最让我骄傲的不是得了多少荣誉,而是看到越来越(yuèláiyuè)多的年轻人接过志愿服务的接力棒,加入“小甜橙”的队伍中来(zhōnglái)。当年背过的瘸腿小伙,如今带(dài)儿子来报名。“恁行不?”“叔,俺娃行,能当‘小甜橙’!”
(高衍 王兆林(wángzhàolín)整理)
地板(dìbǎn)、公交车和担架上,我都睡过
铁路南京站南京南车间客运值班员 万里(wànlǐ)(34岁)
2010年(nián)到2013年大学期间,每年假期做“小甜橙”志愿者时,我都借住在南京(nánjīng)的叔叔家。叔叔在客厅摆了张气垫床,但这床常常漏气,好几次半夜醒来,我发现气漏光了,自己(zìjǐ)就睡在了地上。
叔叔家住在浦口区,和南京火车站正好是157路公交车的首尾两站。每天清晨,我都要赶5点53分的首班公交车前往南京火车站,晚上再(zài)坐末班车回家(huíjiā)。记得201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当了(le)一天(yītiān)“小甜橙”志愿者的我在末班公交车上歪着头睡着了。公交车晃悠了一个半小时(xiǎoshí),我就这样睡了一路。到终点站后,司机(sījī)师傅没注意到我,锁上车门就下班回家了。公交车断电后空调停止运行,20多分钟(duōfēnzhōng)后我被(bèi)冻醒,发现自己身处黑漆漆的公交车停车场,两侧车窗外停满了公交车。我大声呼救了五六分钟,才被其他司机发现并放了出来。
有(yǒu)一次晚上7点多,我把一位拄着拐杖的(de)残疾(cánjí)老师傅从候车室接到了“158雷锋服务站”——“158”的谐音正是“义务帮”。老师傅要坐的火车在第二天凌晨发车,而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上的是“大三班”,每晚11点就下班(xiàbān)了,之后的重点旅客会移交给客运(kèyùn)大班。想到老师傅行动不便还带着大包小包,我始终放心不下。
那天晚上下班(xiàbān)后,我又(yòu)返回了服务站。服务站的几位姐姐都认识我这个(zhègè)大个子志愿者。“你怎么又回来(huílái)了?”她们问道。我解释说,这位老师傅是我领进服务站的,我要负责到底。老师傅人很好,亲切又健谈,等其他人都下班后,我们俩(liǎ)在服务站聊了半宿,直到凌晨把他安全送上车。
那天凌晨过后,公交车早已(zǎoyǐ)停运。服务站(fúwùzhàn)挡板后面放着一部60厘米宽的担架,我就在担架上(shàng)呼呼大睡。那一夜我睡得很沉,连身都没翻,一觉到天亮。
毕业后我进入铁路系统工作,“小甜橙”志愿者马甲换成(huànchéng)了蓝色铁路制服,变的是衣服的颜色,不变的是“人民铁路为(wèi)人民”的初心。现在我当了客运员,看到车站(chēzhàn)的其他(qítā)“小甜橙”在帮助别人的时候,我也会时常怀念那些充满温情的志愿服务时光。
(张耀华(yàohuá) 李锐整理)
橙背心,蓝警服,都是为旅客服务(fúwù)
安徽警官(jǐngguān)职业学院学生 卓浩然(20岁)
穿(chuān)上警服,旅客会称呼我“同志(tóngzhì)”。在警服外套上“小甜橙”的马甲,旅客明显和我亲近了,喊我“小伙子”。
我是一名大二的警校(jǐngxiào)生,平时少言寡语。今年春运在合肥火车站参加“小甜橙”志愿(zhìyuàn)服务,一方面我想通过志愿服务学习如何帮助群众、怎样和群众进行沟通;另一方面,铁路有句口号“人民铁路为(wèi)(wèi)人民”,警务队伍里也有“人民警察为人民”,是相通的。
志愿服务的第一天,我和(hé)59位同学在合肥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列队。寒风中,教官面朝着队伍(duìwǔ)大声说:“你们都是预备警官,要向旅客展示出警务队伍的精神风貌。”所有人的背都下意识地(dì)挺直了。
“小甜橙”的志愿服务内容(nèiróng)不算辛苦,虽然也要多站多走,但和警校里的体能训练相比是小巫见大巫。我的服务岗位在车站(chēzhàn)的进站口(kǒu),主要工作是将进站乘车(chéngchē)的旅客分散引导至各个安检口,维持现场秩序,保持进站通道相对通畅。也有(yǒu)很多旅客会向我咨询问路,“购票窗口怎么走”“怎么下到停车场接人”,我都会热情地给他们解答。
农历小年的(de)(de)前后几天,合肥火车站(huǒchēzhàn)的客流明显增大(zēngdà),为了更好(gènghǎo)地开展志愿服务,我们在(zài)“小甜橙”的橙色背心下面穿上了藏蓝色的警服。警服不仅仅是职业的身份标识,更象征着(zhe)群众对人民警察的信任。有一位学弟说:“穿着警服,连痒痒都不敢随便抓,生怕有什么不雅观的动作让人瞧见,丢人民警察的脸。”但穿上警服后,引导旅客的效率明显提高。在引导人流时,通过一个简单的手势,或者一句温和的指引,旅客就能立刻响应(xiǎngyìng)。这种信任让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,也更加坚定了我要认真服务每一位旅客的决心。
从有距离感的(de)“同志”到亲切的“小伙子”,让我渐渐明白:这身警服赋予我们的不仅是(shì)威严,更是沉甸甸的责任;而(ér)这件橙马甲教会我们的不仅是服务,更是心与心交流的温度。
(孙文郡(jùn) 张家祺整理)
铁路淮南西站团委书记 李玉镜(lǐyùjìng)(34岁)
“老师,你们什么(shénme)时(shí)候再来?不走好不好?”5年多的时间里,每次和孩子们分别时,我总会把脸侧(liǎncè)开,生怕被孩子们看见眼眶里的泪水。
柯湖小(xiǎo)学(xiǎoxué)位于瓦蚌湖畔,是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最偏远的一所学校,学校里近一半的学生是留守(liúshǒu)儿童,师资(shīzī)力量也有些薄弱。“梦想计划”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(yǒuxiàngōngsī)团委发起的综合性志愿服务项目,先后推出了“梦想课堂”“梦想书桌”和“梦想夏令营(xiàlìngyíng)”。自2020年暑期开始,我和数十名师范专业的“小甜橙”走出铁路、走进乡镇小学,为留守农村的孩子们送去关爱。
“梦想课堂”的第一站(dìyīzhàn)就是柯湖小学。孩子们那充满好奇的眼神,瞬间勾起了我的回忆。我在安徽(ānhuī)的农村(nóngcūn)长大,不少同学也是留守儿童。透过一张张被晒得黝黑的稚嫩脸庞,我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童年玩伴。
我自告奋勇给孩子(háizi)们上第一节课。多年没有站上讲台,我还有点小紧张,但我感觉孩子们的小表情(biǎoqíng)比我还紧张——个个正襟危坐(zhèngjīnwēizuò),胳膊平放在桌面上,后背挺得溜直,回答问题时也扭捏害羞、热情不高。我想,孩子们对我还不够熟悉,大家还没有玩开(wánkāi)。
上完第一节课(kè),我与几位“小甜橙”老师商量了(le)一下,将“魔术”趣味课提前,先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。
我们把两张课桌拼在一起(yìqǐ),铺上魔术台布。20多个(duōgè)孩子(háizi)(háizi)围了几圈,外层的孩子只能从人墙的缝隙里把小脑袋探进来。表演魔术的是我们单位的小吴,小吴用两根手指撑开(chēngkāi)橡皮筋,把另一个橡皮筋套在孩子的手上,然后一个动作两个橡皮筋就嵌套在了一起。这只是个入门(rùmén)魔术级别的“小把戏”,孩子们却(què)接连发出惊叹,“哇”声一片……一个个小魔术让孩子们的双眼越瞪越大,我们和孩子们也越来越亲近,课堂氛围瞬间热闹起来。
不是所有孩子都能(néng)在社交中勇敢地踏出第一步。许多留守儿童内心炙热,但缺乏主动亲近(qīnjìn)身边人(rén)的(de)勇气。“梦想课堂”的初衷(chūzhōng)是帮助孩子们提高学业成绩,第一期课程结束后,我认识到“梦想课堂”更要去除孩子们的“孤单”、增添生活的“色彩(sècǎi)”。我把音乐、手工、体能作为重要内容,陪着孩子们一起唱歌,一起做手工,一起玩耍。校园里响起了悠扬的琴声,墙面上挂起了多彩的手工作品,操场上出现了少年(shàonián)雀跃的身影。
后来(hòulái),柯湖小学和堆坊(duīfāng)小学合并到了孙庙(sūnmiào)小学,“梦想课堂”也跟着来到了孙庙小学。孩子的数量增多了,志愿者的队伍也更加壮大(zhuàngdà)。我通过开设“梦想夏令营”,组织孩子们在暑假分批次前往红色教育基地、文化博物馆、高铁车站等处参观学习,开阔视野。“梦想书桌”计划推出时,我立刻为孙庙小学申请了9张书桌。今年春节前夕,“小甜橙”抬着书桌,送进四年级二班的范敬恩(fànjìngēn)(fànjìngēn)家中。她迫不及待地坐上去体验,向我们分享了她想怎样使用这张书桌——这里(lǐ)可以(kěyǐ)放文具,那里可以放课本,桌膛里可以放书包。高铁元素的书桌引得范敬恩的两个弟弟也凑上来东摸摸西(xī)瞧瞧。
“镜姐,下次再来一定带上我,和孩子们在一起可(kě)开心了。”“小甜橙(tiánchéng)”让(ràng)孩子们的童年不再缺少陪伴,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让“小甜橙”回到了美好的童年。
(张(zhāng)耀华 蔡东然整理)
“甜橙”不言(yán),下自成蹊
扬州大学退休教师(jiàoshī) 朱立祥(66岁)
我有一枚橙色(chéngsè)的徽章,一直放在书房的抽屉里,上面印着一颗胖橙子。2013年1月,扬州(yángzhōu)火车站开展“小甜橙”志愿服务,我带着学生(xuéshēng)作为首批社会志愿者参与其中。春运结束时,铁路部门送给我这枚徽章以作纪念(jìniàn)。
50多岁的人穿上(shàng)“小甜橙”的马甲,我(wǒ)还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是旅客明显更信任(xìnrèn)我,觉得我“老成持重,在一群毛头小子里一看就是个管事的”。我当年的那批“小甜橙”学生,早就分散在了天南海北。但每次我看到车站里的“小甜橙”,还能想起他们(tāmen)。
2025年春运(chūnyùn),我站在扬州东站进站口处(kǒuchù),看着几个被教学资料塞得满满当当(mǎnmǎndāngdāng)的纸箱犯了难。我还在琢磨着怎么把沉重的纸箱弄上车时,一抹橙色身影快步向我走来。
“大爷,我帮(bāng)您把行李送到检票口吧。”一位穿着“小甜橙”马甲(mǎjiǎ)的志愿者小周(zhōu)蹲下身,把纸箱搬到行李推车上,熟练地用防滑绑带固定好,抬头时(shí)她的镜片上蒙了一层白雾。当年的志愿者,今天也成了体验志愿服务的旅客。
看着她忙碌的身影,我(wǒ)感慨万千,仿佛回到了十几年(shíjǐnián)前。“谢谢,你们现在的装备比我们那(nà)时候齐全多啦。”我忍不住开口和她聊了几句,思绪渐渐飘回2013年的冬天。
那时(nàshí)我还没退休,寒假带着班里的孩子们参加春运志愿服务。当年我们帮一位(yīwèi)农民工大哥搬行李(xínglǐ),几个人手提肩扛,才抬动他的蛇皮袋。大哥塞给我的学生一把花生,“自家种的,香”。
我从帆布包里掏出泛黄的志愿者证书给(gěi)志愿者小周(zhōu)看,她的语气里多了几分敬意。看着小周,我又一次想起了十几年前的学生。“我们那时候,服务台(fúwùtái)是一张约3米长的木桌子(zhuōzi),条件虽然艰苦,却挡不住我们的热情。”我和小周在服务台聊天(liáotiān),“也没有这么多智能设备,全靠腿勤、嘴勤、手勤。”
当年我们手里攥着手写的列车时刻表,遇到旅客询问车次就翻查看看(kànkàn)。小周指着墙上的“小甜橙”服务地图说:“现在旅客扫个码就能找到志愿者,您(nín)当年肯定没有(méiyǒu)吧。”
我记得最清晰的一件事是,有一年大年初六,一位(yīwèi)抱着婴儿的母亲在候车室急得直哭——孩子的奶粉喝完了。一位爱心旅客慷慨提供了奶粉,但这位母亲没带(méidài)奶瓶,奶粉是在我自己的保温杯里冲(chōng)的。我把保温杯递给那位母亲,孩子咕嘟(gūdū)咕嘟喝下去,母亲连声道谢(dàoxiè):“你们比亲人还贴心。”
检票口前,小(xiǎo)周递给我(wǒ)一张印着志愿者联系方式的爱心卡片:“大爷,到站后有人接您吗?需要帮助就打这个电话。”我接过卡片,指尖轻轻摩挲着“小甜橙”的橙色logo。我又想起自己那枚印着“小甜橙”图案的徽章,底色有些褪色(tuìshǎi)了,但还是(háishì)温暖的橙色。
(黄悦 徐晨整理(zhěnglǐ))
铁路上海站(shànghǎizhàn)团委副书记 吕洲豪(32岁)
2025年上海南站候车大厅(dàtīng)的(de)换乘通道里,我看到(kàndào)“小甜橙”符媛婷正在为外国旅客引导乘车路线,“小甜橙”游园在售票窗口(chuāngkǒu)一边手速惊人地敲(qiāo)着键盘,一边用流利的英语应答外国旅客。她们的双语服务仿佛穿越时光,让我想起了2010年我在售票窗口苦练英语口语的时候。
2010年(nián)5月1日,世博会开幕式前夜,我在上海站“双语售票窗”后,攥着《世博导览手册(shǒucè)》反复默记。作为首批(shǒupī)服务世博的铁路(tiělù)志愿者,每天要(yào)回答200余次“如何前往世博园”,用英语为外国游客解释“高铁与地铁的换乘规则”。当年的我“菜”得很,只能将固定回答背得烂熟于胸,有旅客来咨询时就像(xiàng)报菜名一样一口气全背出来。
最让我担心的,是(shì)外国(wàiguó)旅客提出没有(méiyǒu)事前准备过答案的问题。好在我的“塑料英语(yīngyǔ)”还算过关,大部分场景都应付得来。第一次用英语成功帮助德国游客时,他竖起了大拇指,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什么是“青春与时代同频”。
当年虽然“菜”,但有一腔热忱,成功帮助到旅客(lǚkè)时总会特别兴奋。回忆起世博期间的“小甜橙”服务经历,我仍热血(rèxuè)澎湃。
世博会(shìbóhuì)落幕,但“小甜橙”的(de)志愿(zhìyuàn)之火仍(réng)在上海站持续燃烧,每年的春运志愿服务都有世博会时(shí)的影子。当年的“小白菜”(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对园区志愿者的昵称),用青春诠释了“世界在你眼前,我们在你身边”,如今的“小甜橙”正用“橙心橙意”续写新的服务篇章。
军旅生涯和志愿服务是(shì)我青春故事的上下篇
浙江理工大学(lǐgōngdàxué)科技与艺术学院学生 沈健(27岁)
2017年到2022年,我(wǒ)在部队服役5年,成为一名炮兵。退役后到杭州读大学,当了3年的“小(xiǎo)甜橙”志愿者。5年军旅生涯,3年志愿服务,构成了我青春故事的上下篇章。至今仍记得2018年那个冬天,我们(wǒmen)部队接到(jiēdào)紧急任务,协助市政部门清理道路积雪。夜幕下,漫天飞雪拍打着我和战友们的脸庞,气温骤降至冰点,我们奋战至凌晨时分。作为军人,执行命令(zhíxíngmìnglìng)没有“自愿”可言。但对我个人而言,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却成为我志愿服务的启蒙(qǐméng)时刻(shíkè)。
志愿服务期间,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旅客:不(bù)熟悉车站布局的、不懂换乘流程的、行动不便需要特殊照顾的。每当我为他们指路、解答疑问、提供帮助后,送上一声祝福、递(dì)上一杯(yībēi)热茶,收获他们真诚的感谢和笑脸时,内心都(dōu)充满自豪。节假日坚守在志愿服务一线,虽然错过了与家人团聚,却收获了更多感动(gǎndòng)与成长。
今年1月25日,我(wǒ)在杭州东站(dōngzhàn)志愿服务时,发现出站口有位老大爷正在徘徊。大爷头发花白,佝偻着背,一手拎着袋子,一手拄着拐杖,步履蹒跚,每次只能挪动一个脚掌的距离(jùlí)。我立即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。大爷操着浓重的方言,急得满头大汗,反复说着:“打给我女儿,打给我女儿。”我接过(jiēguò)他的老式按键手机,发现已经没(méi)电关机了,大爷还不停(bùtíng)地重复:“可以打的,可以打的……”
我(wǒ)(wǒ)找来充电宝给手机(shǒujī)充上电,终于联系上了(le)大爷的(de)(de)女儿(nǚér)。原来大爷是从宁波出发,要在杭州转车去女儿家过年。女儿只买了到杭州的车票,下一程需要大爷自己(zìjǐ)购票。大爷从身上掏出一把零钱和一张纸质临时身份证明——他的身份证遗失了。“使用临时身份证明只能在人工窗口购票,我现在带您过去。”“好,好……”我立即呼叫支援,和另一位“小甜橙”一起搀扶大爷前往最东边的人工售票窗口。在我们的帮助下,大爷的步履明显轻快了许多,虽然听不清他具体说什么,但他脸上的笑容传递着满满的谢意。
而今(érjīn)回首,从保家卫国到(dào)服务群众,变的(de)是身份与场景,不变(bùbiàn)的是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。每当看见旅客们舒展的眉头和会心的微笑,我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风雪夜——原来,军人的担当与志愿者的热忱本就一脉相承。
(张(zhāng)耀华 陈宇昂整理)
商城之窗的双语(shuāngyǔ)“谢谢”
金华车务段义乌站(zhàn)客运员 吕顺楠(29岁)
义乌可能是“老外(lǎowài)”最多的中国县级市。2025年(nián)“五一”期间,义乌站每70名进站旅客中便有一位是外籍人士,候车厅俨然成了(le)一个“微型联合国”。
我经常会被自己的“没眼力见儿”给逗乐——对(duì)着新疆旅客狂秀英语,转头又对着日韩(hán)旅客大讲(dàjiǎng)中文。最慌的是碰见讲阿拉伯语、意大利语等小语种的旅客,那必定是手忙脚乱(shǒumángjiǎoluàn),恨不得立刻教会他们说中文。
阿拉伯客商如今在义乌常驻外商中占(zhàn)比有三成多。车务段要为“小(xiǎo)甜橙”专门进行阿拉伯语培训,扭成新月状的字母属实让我焦头烂额(jiāotóulàné)。然而一想到能成为穿梭在客流里的“语言(yǔyán)桥梁”,我心中就不免燃起了期待。
“shu—ke—lan!”在带头练习(liànxí)“谢谢(xièxiè)”的发音时,我才发现阿拉伯语远比想象中还要(yào)复杂。“注意这个(zhègè)颤音。”来自也门的留学生王迪老师轻点自己的喉结(hóujié),“这个颤音要胸腔用力,从深处震动,就好像骆驼脖子上的驼铃。”当(dāng)20多个“小甜橙”异口同声发出“شكرا(谢谢)”,窗外中欧班列的货车轰隆驶过,挤压铁轨的金属声与我们的练习声交织在一起。
“五一”期间,候车厅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(de)脚步声,一个头戴红色头巾、眉头(méitóu)紧锁的年轻男子冲到我(wǒ)的面前。我迅速捕捉到“جواز سفر”——这是王迪教过的“护照”!猜到了他的来意,我赶紧用(yòng)手指比画出(chū)长方形,然后摇摇手,有些不自信地用英文夹杂着阿拉伯语问他:“No جواز سفر(没有护照)?”
他竟然理解了我的“混搭外语”,眼睛“唰”地亮了,猛猛点头。我一边用对讲机联系各(gè)岗位询问是否有捡到护照,一边带着(zhe)他从进站口重新找了一遍。好在最后在安检台找到(zhǎodào)——原来他掏东西时顺手把护照放在了那儿。接过(jiēguò)护照的那一刻,他长舒了一口气,皱着的眉头也舒展开来,不停(bùtíng)地对我说“شكرا(谢谢)”。
一开始,面对形形色色的(de)(de)“异乡客”时,我只能磕磕巴巴地与他们(tāmen)交流,后来我学会了(le)“猜谜”:从复杂的外语中提取关键字,再去尝试与他们沟通。现在还用(yòng)上了高科技,遇上陌生的语言时,就用翻译机为国际旅客排忧解难。如今,在义乌站(zhàn)有越来越多戴着(zhe)阿拉伯头巾的商人(shāngrén)会用中文说“谢谢”,穿橙色马甲的我们已经越来越熟练用“شكرا(谢谢)”回应。横跨亚欧非的广袤大地上,一列列钢铁驼队载着的不仅是商品,还有无数个“شكرا(谢谢)”与“谢谢”的故事,一起驶向远方。
(张耀华 卓叶迪(zhuóyèdí)整理)
阜阳市心公益(gōngyì)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程里成(38岁)
“俺叫程里成,年轻(niánqīng)时是‘小甜橙’,现在是‘老甜橙’咯!”2008年到2025年,从毛头小子(máotóuxiǎozi)变成中年大叔,志愿服务这件事我坚持了18年。我手机(shǒujī)里还存着(cúnzhe)2008年第一次参加铁路志愿服务时的(de)照片:那年我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穿的是红马甲,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。
2010年前后,铁路部门新发了一批橙色的马甲,前胸和后背写着“铁路志愿者”。我们(wǒmen)红橙两款(liǎngkuǎn)混着(hùnzhe)穿,旅客见了以为我们不是一个队伍,“恁(你)们是一拨人不?”后来,志愿者逐步换装成橙马甲,2016年,马甲上又加上了“小甜橙(tiánchéng)”的图案。
阜阳站重点旅客(lǚkè)以前全靠背,说出去很多人(rén)都不理解(lǐjiě)。2019年之前的春运,我每天都能背二三十个重点旅客。一方面,我要给其他志愿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;另一方面,有些志愿者年龄小、经验(jīngyàn)少,我不放心。万一把旅客摔了可咋整?
“节后春运(chūnyùn)看(kàn)阜阳”,阜阳站初建时算是个大站,但是随着旅客流量越来越大,基础设施有些跟不上:只有最东边的(de)站台有一部(yībù)电梯,有坡道的行包通道又特别远,提前半个小时就要出发。只有遇到骨折等不能背的重点旅客,我才会推着旅客走行包通道。
今年春运,我一周服务的重点旅客还没有以前一天多(duō)。2019年,阜阳西站开通,高铁站分走了(le)老火车站一半的客流,老站的重点旅客更是大量减少——外出就医的重点旅客为了赶时间,都会选择(xuǎnzé)从西站坐(zuò)高铁出行。阜阳站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造,便捷通道(tōngdào)增多了,各个站台都增设了电梯,不能行走的旅客再也不用志愿者背上背下了。
很多(hěnduō)农民工的子女,假期会从阜阳站坐火车投奔父母,这些(zhèxiē)孩子被我们称为“小(xiǎo)候鸟”。我亲眼见过一个邻居领着十几个孩子乘车,排成一串就像一列小火车。“小候鸟”大多选择绿皮车,从阜阳到徐州。
半大不大的小孩(xiǎohái)待不住,一群娃子聚在(zài)一起更是“无法无天(wúfǎwútiān)”。尤其是农村小孩,可能从小到大第一次坐火车,看什么都新奇。“小候鸟”在火车站里叽叽喳喳,到处乱跑。管是管不住(guǎnbúzhù)的,堵不如疏,不如给孩子(háizi)找个渠道。于是,我们把孩子集中起来,在候车室里领着孩子玩。
阜阳站在母婴候车室里划了个区域,我们在里面铺上爬爬垫,小孩也(yě)不用脱鞋,在爬爬垫上一坐,就不需要座位了。刚开始的时候,我领(wǒlǐng)着孩子看书,后来,我们又添置了一批玩具(wánjù),孩子就都能坐住(zhù)了。这个项目我们一直持续到现在,高铁通车之后还引入了高铁站。
2024年冬天,我们(men)团队在阜阳西站也设立了“小候鸟(hòuniǎo)驿站(yìzhàn)”,给返乡的孩子们准备书包、绘本和热乎乎的饭菜,在驿站里给孩子们辅导作业,和孩子们一起画画、做游戏。我最欣慰的画面(huàmiàn),便是孩子们抱着橙子玩偶时露出的笑脸,“瞅这娃笑的模样”。
从“红马甲”到“橙马甲”,从背着旅客上下站台到见证无障碍设施(shèshī)完善,我见证了铁路服务(fúwù)的变迁,也见证了志愿精神的传承。那些被汗水浸透的岁月,那些被笑脸温暖的时光(shíguāng),都化作生命中最珍贵(zhēnguì)的记忆。18年来,最让我骄傲的不是得了多少荣誉,而是看到越来越(yuèláiyuè)多的年轻人接过志愿服务的接力棒,加入“小甜橙”的队伍中来(zhōnglái)。当年背过的瘸腿小伙,如今带(dài)儿子来报名。“恁行不?”“叔,俺娃行,能当‘小甜橙’!”
(高衍 王兆林(wángzhàolín)整理)
地板(dìbǎn)、公交车和担架上,我都睡过
铁路南京站南京南车间客运值班员 万里(wànlǐ)(34岁)
2010年(nián)到2013年大学期间,每年假期做“小甜橙”志愿者时,我都借住在南京(nánjīng)的叔叔家。叔叔在客厅摆了张气垫床,但这床常常漏气,好几次半夜醒来,我发现气漏光了,自己(zìjǐ)就睡在了地上。
叔叔家住在浦口区,和南京火车站正好是157路公交车的首尾两站。每天清晨,我都要赶5点53分的首班公交车前往南京火车站,晚上再(zài)坐末班车回家(huíjiā)。记得201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当了(le)一天(yītiān)“小甜橙”志愿者的我在末班公交车上歪着头睡着了。公交车晃悠了一个半小时(xiǎoshí),我就这样睡了一路。到终点站后,司机(sījī)师傅没注意到我,锁上车门就下班回家了。公交车断电后空调停止运行,20多分钟(duōfēnzhōng)后我被(bèi)冻醒,发现自己身处黑漆漆的公交车停车场,两侧车窗外停满了公交车。我大声呼救了五六分钟,才被其他司机发现并放了出来。
有(yǒu)一次晚上7点多,我把一位拄着拐杖的(de)残疾(cánjí)老师傅从候车室接到了“158雷锋服务站”——“158”的谐音正是“义务帮”。老师傅要坐的火车在第二天凌晨发车,而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上的是“大三班”,每晚11点就下班(xiàbān)了,之后的重点旅客会移交给客运(kèyùn)大班。想到老师傅行动不便还带着大包小包,我始终放心不下。
那天晚上下班(xiàbān)后,我又(yòu)返回了服务站。服务站的几位姐姐都认识我这个(zhègè)大个子志愿者。“你怎么又回来(huílái)了?”她们问道。我解释说,这位老师傅是我领进服务站的,我要负责到底。老师傅人很好,亲切又健谈,等其他人都下班后,我们俩(liǎ)在服务站聊了半宿,直到凌晨把他安全送上车。
那天凌晨过后,公交车早已(zǎoyǐ)停运。服务站(fúwùzhàn)挡板后面放着一部60厘米宽的担架,我就在担架上(shàng)呼呼大睡。那一夜我睡得很沉,连身都没翻,一觉到天亮。
毕业后我进入铁路系统工作,“小甜橙”志愿者马甲换成(huànchéng)了蓝色铁路制服,变的是衣服的颜色,不变的是“人民铁路为(wèi)人民”的初心。现在我当了客运员,看到车站(chēzhàn)的其他(qítā)“小甜橙”在帮助别人的时候,我也会时常怀念那些充满温情的志愿服务时光。
(张耀华(yàohuá) 李锐整理)
橙背心,蓝警服,都是为旅客服务(fúwù)
安徽警官(jǐngguān)职业学院学生 卓浩然(20岁)
穿(chuān)上警服,旅客会称呼我“同志(tóngzhì)”。在警服外套上“小甜橙”的马甲,旅客明显和我亲近了,喊我“小伙子”。
我是一名大二的警校(jǐngxiào)生,平时少言寡语。今年春运在合肥火车站参加“小甜橙”志愿(zhìyuàn)服务,一方面我想通过志愿服务学习如何帮助群众、怎样和群众进行沟通;另一方面,铁路有句口号“人民铁路为(wèi)(wèi)人民”,警务队伍里也有“人民警察为人民”,是相通的。
志愿服务的第一天,我和(hé)59位同学在合肥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列队。寒风中,教官面朝着队伍(duìwǔ)大声说:“你们都是预备警官,要向旅客展示出警务队伍的精神风貌。”所有人的背都下意识地(dì)挺直了。
“小甜橙”的志愿服务内容(nèiróng)不算辛苦,虽然也要多站多走,但和警校里的体能训练相比是小巫见大巫。我的服务岗位在车站(chēzhàn)的进站口(kǒu),主要工作是将进站乘车(chéngchē)的旅客分散引导至各个安检口,维持现场秩序,保持进站通道相对通畅。也有(yǒu)很多旅客会向我咨询问路,“购票窗口怎么走”“怎么下到停车场接人”,我都会热情地给他们解答。
农历小年的(de)(de)前后几天,合肥火车站(huǒchēzhàn)的客流明显增大(zēngdà),为了更好(gènghǎo)地开展志愿服务,我们在(zài)“小甜橙”的橙色背心下面穿上了藏蓝色的警服。警服不仅仅是职业的身份标识,更象征着(zhe)群众对人民警察的信任。有一位学弟说:“穿着警服,连痒痒都不敢随便抓,生怕有什么不雅观的动作让人瞧见,丢人民警察的脸。”但穿上警服后,引导旅客的效率明显提高。在引导人流时,通过一个简单的手势,或者一句温和的指引,旅客就能立刻响应(xiǎngyìng)。这种信任让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,也更加坚定了我要认真服务每一位旅客的决心。
从有距离感的(de)“同志”到亲切的“小伙子”,让我渐渐明白:这身警服赋予我们的不仅是(shì)威严,更是沉甸甸的责任;而(ér)这件橙马甲教会我们的不仅是服务,更是心与心交流的温度。
(孙文郡(jùn) 张家祺整理)
铁路淮南西站团委书记 李玉镜(lǐyùjìng)(34岁)
“老师,你们什么(shénme)时(shí)候再来?不走好不好?”5年多的时间里,每次和孩子们分别时,我总会把脸侧(liǎncè)开,生怕被孩子们看见眼眶里的泪水。
柯湖小(xiǎo)学(xiǎoxué)位于瓦蚌湖畔,是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最偏远的一所学校,学校里近一半的学生是留守(liúshǒu)儿童,师资(shīzī)力量也有些薄弱。“梦想计划”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(yǒuxiàngōngsī)团委发起的综合性志愿服务项目,先后推出了“梦想课堂”“梦想书桌”和“梦想夏令营(xiàlìngyíng)”。自2020年暑期开始,我和数十名师范专业的“小甜橙”走出铁路、走进乡镇小学,为留守农村的孩子们送去关爱。
“梦想课堂”的第一站(dìyīzhàn)就是柯湖小学。孩子们那充满好奇的眼神,瞬间勾起了我的回忆。我在安徽(ānhuī)的农村(nóngcūn)长大,不少同学也是留守儿童。透过一张张被晒得黝黑的稚嫩脸庞,我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童年玩伴。
我自告奋勇给孩子(háizi)们上第一节课。多年没有站上讲台,我还有点小紧张,但我感觉孩子们的小表情(biǎoqíng)比我还紧张——个个正襟危坐(zhèngjīnwēizuò),胳膊平放在桌面上,后背挺得溜直,回答问题时也扭捏害羞、热情不高。我想,孩子们对我还不够熟悉,大家还没有玩开(wánkāi)。
上完第一节课(kè),我与几位“小甜橙”老师商量了(le)一下,将“魔术”趣味课提前,先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。
我们把两张课桌拼在一起(yìqǐ),铺上魔术台布。20多个(duōgè)孩子(háizi)(háizi)围了几圈,外层的孩子只能从人墙的缝隙里把小脑袋探进来。表演魔术的是我们单位的小吴,小吴用两根手指撑开(chēngkāi)橡皮筋,把另一个橡皮筋套在孩子的手上,然后一个动作两个橡皮筋就嵌套在了一起。这只是个入门(rùmén)魔术级别的“小把戏”,孩子们却(què)接连发出惊叹,“哇”声一片……一个个小魔术让孩子们的双眼越瞪越大,我们和孩子们也越来越亲近,课堂氛围瞬间热闹起来。
不是所有孩子都能(néng)在社交中勇敢地踏出第一步。许多留守儿童内心炙热,但缺乏主动亲近(qīnjìn)身边人(rén)的(de)勇气。“梦想课堂”的初衷(chūzhōng)是帮助孩子们提高学业成绩,第一期课程结束后,我认识到“梦想课堂”更要去除孩子们的“孤单”、增添生活的“色彩(sècǎi)”。我把音乐、手工、体能作为重要内容,陪着孩子们一起唱歌,一起做手工,一起玩耍。校园里响起了悠扬的琴声,墙面上挂起了多彩的手工作品,操场上出现了少年(shàonián)雀跃的身影。
后来(hòulái),柯湖小学和堆坊(duīfāng)小学合并到了孙庙(sūnmiào)小学,“梦想课堂”也跟着来到了孙庙小学。孩子的数量增多了,志愿者的队伍也更加壮大(zhuàngdà)。我通过开设“梦想夏令营”,组织孩子们在暑假分批次前往红色教育基地、文化博物馆、高铁车站等处参观学习,开阔视野。“梦想书桌”计划推出时,我立刻为孙庙小学申请了9张书桌。今年春节前夕,“小甜橙”抬着书桌,送进四年级二班的范敬恩(fànjìngēn)(fànjìngēn)家中。她迫不及待地坐上去体验,向我们分享了她想怎样使用这张书桌——这里(lǐ)可以(kěyǐ)放文具,那里可以放课本,桌膛里可以放书包。高铁元素的书桌引得范敬恩的两个弟弟也凑上来东摸摸西(xī)瞧瞧。
“镜姐,下次再来一定带上我,和孩子们在一起可(kě)开心了。”“小甜橙(tiánchéng)”让(ràng)孩子们的童年不再缺少陪伴,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让“小甜橙”回到了美好的童年。
(张(zhāng)耀华 蔡东然整理)
“甜橙”不言(yán),下自成蹊
扬州大学退休教师(jiàoshī) 朱立祥(66岁)
我有一枚橙色(chéngsè)的徽章,一直放在书房的抽屉里,上面印着一颗胖橙子。2013年1月,扬州(yángzhōu)火车站开展“小甜橙”志愿服务,我带着学生(xuéshēng)作为首批社会志愿者参与其中。春运结束时,铁路部门送给我这枚徽章以作纪念(jìniàn)。
50多岁的人穿上(shàng)“小甜橙”的马甲,我(wǒ)还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是旅客明显更信任(xìnrèn)我,觉得我“老成持重,在一群毛头小子里一看就是个管事的”。我当年的那批“小甜橙”学生,早就分散在了天南海北。但每次我看到车站里的“小甜橙”,还能想起他们(tāmen)。
2025年春运(chūnyùn),我站在扬州东站进站口处(kǒuchù),看着几个被教学资料塞得满满当当(mǎnmǎndāngdāng)的纸箱犯了难。我还在琢磨着怎么把沉重的纸箱弄上车时,一抹橙色身影快步向我走来。
“大爷,我帮(bāng)您把行李送到检票口吧。”一位穿着“小甜橙”马甲(mǎjiǎ)的志愿者小周(zhōu)蹲下身,把纸箱搬到行李推车上,熟练地用防滑绑带固定好,抬头时(shí)她的镜片上蒙了一层白雾。当年的志愿者,今天也成了体验志愿服务的旅客。
看着她忙碌的身影,我(wǒ)感慨万千,仿佛回到了十几年(shíjǐnián)前。“谢谢,你们现在的装备比我们那(nà)时候齐全多啦。”我忍不住开口和她聊了几句,思绪渐渐飘回2013年的冬天。
那时(nàshí)我还没退休,寒假带着班里的孩子们参加春运志愿服务。当年我们帮一位(yīwèi)农民工大哥搬行李(xínglǐ),几个人手提肩扛,才抬动他的蛇皮袋。大哥塞给我的学生一把花生,“自家种的,香”。
我从帆布包里掏出泛黄的志愿者证书给(gěi)志愿者小周(zhōu)看,她的语气里多了几分敬意。看着小周,我又一次想起了十几年前的学生。“我们那时候,服务台(fúwùtái)是一张约3米长的木桌子(zhuōzi),条件虽然艰苦,却挡不住我们的热情。”我和小周在服务台聊天(liáotiān),“也没有这么多智能设备,全靠腿勤、嘴勤、手勤。”
当年我们手里攥着手写的列车时刻表,遇到旅客询问车次就翻查看看(kànkàn)。小周指着墙上的“小甜橙”服务地图说:“现在旅客扫个码就能找到志愿者,您(nín)当年肯定没有(méiyǒu)吧。”
我记得最清晰的一件事是,有一年大年初六,一位(yīwèi)抱着婴儿的母亲在候车室急得直哭——孩子的奶粉喝完了。一位爱心旅客慷慨提供了奶粉,但这位母亲没带(méidài)奶瓶,奶粉是在我自己的保温杯里冲(chōng)的。我把保温杯递给那位母亲,孩子咕嘟(gūdū)咕嘟喝下去,母亲连声道谢(dàoxiè):“你们比亲人还贴心。”
检票口前,小(xiǎo)周递给我(wǒ)一张印着志愿者联系方式的爱心卡片:“大爷,到站后有人接您吗?需要帮助就打这个电话。”我接过卡片,指尖轻轻摩挲着“小甜橙”的橙色logo。我又想起自己那枚印着“小甜橙”图案的徽章,底色有些褪色(tuìshǎi)了,但还是(háishì)温暖的橙色。
(黄悦 徐晨整理(zhěnglǐ))
铁路上海站(shànghǎizhàn)团委副书记 吕洲豪(32岁)
2025年上海南站候车大厅(dàtīng)的(de)换乘通道里,我看到(kàndào)“小甜橙”符媛婷正在为外国旅客引导乘车路线,“小甜橙”游园在售票窗口(chuāngkǒu)一边手速惊人地敲(qiāo)着键盘,一边用流利的英语应答外国旅客。她们的双语服务仿佛穿越时光,让我想起了2010年我在售票窗口苦练英语口语的时候。
2010年(nián)5月1日,世博会开幕式前夜,我在上海站“双语售票窗”后,攥着《世博导览手册(shǒucè)》反复默记。作为首批(shǒupī)服务世博的铁路(tiělù)志愿者,每天要(yào)回答200余次“如何前往世博园”,用英语为外国游客解释“高铁与地铁的换乘规则”。当年的我“菜”得很,只能将固定回答背得烂熟于胸,有旅客来咨询时就像(xiàng)报菜名一样一口气全背出来。
最让我担心的,是(shì)外国(wàiguó)旅客提出没有(méiyǒu)事前准备过答案的问题。好在我的“塑料英语(yīngyǔ)”还算过关,大部分场景都应付得来。第一次用英语成功帮助德国游客时,他竖起了大拇指,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什么是“青春与时代同频”。
当年虽然“菜”,但有一腔热忱,成功帮助到旅客(lǚkè)时总会特别兴奋。回忆起世博期间的“小甜橙”服务经历,我仍热血(rèxuè)澎湃。
世博会(shìbóhuì)落幕,但“小甜橙”的(de)志愿(zhìyuàn)之火仍(réng)在上海站持续燃烧,每年的春运志愿服务都有世博会时(shí)的影子。当年的“小白菜”(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对园区志愿者的昵称),用青春诠释了“世界在你眼前,我们在你身边”,如今的“小甜橙”正用“橙心橙意”续写新的服务篇章。
军旅生涯和志愿服务是(shì)我青春故事的上下篇
浙江理工大学(lǐgōngdàxué)科技与艺术学院学生 沈健(27岁)
2017年到2022年,我(wǒ)在部队服役5年,成为一名炮兵。退役后到杭州读大学,当了3年的“小(xiǎo)甜橙”志愿者。5年军旅生涯,3年志愿服务,构成了我青春故事的上下篇章。至今仍记得2018年那个冬天,我们(wǒmen)部队接到(jiēdào)紧急任务,协助市政部门清理道路积雪。夜幕下,漫天飞雪拍打着我和战友们的脸庞,气温骤降至冰点,我们奋战至凌晨时分。作为军人,执行命令(zhíxíngmìnglìng)没有“自愿”可言。但对我个人而言,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却成为我志愿服务的启蒙(qǐméng)时刻(shíkè)。
志愿服务期间,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旅客:不(bù)熟悉车站布局的、不懂换乘流程的、行动不便需要特殊照顾的。每当我为他们指路、解答疑问、提供帮助后,送上一声祝福、递(dì)上一杯(yībēi)热茶,收获他们真诚的感谢和笑脸时,内心都(dōu)充满自豪。节假日坚守在志愿服务一线,虽然错过了与家人团聚,却收获了更多感动(gǎndòng)与成长。
今年1月25日,我(wǒ)在杭州东站(dōngzhàn)志愿服务时,发现出站口有位老大爷正在徘徊。大爷头发花白,佝偻着背,一手拎着袋子,一手拄着拐杖,步履蹒跚,每次只能挪动一个脚掌的距离(jùlí)。我立即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。大爷操着浓重的方言,急得满头大汗,反复说着:“打给我女儿,打给我女儿。”我接过(jiēguò)他的老式按键手机,发现已经没(méi)电关机了,大爷还不停(bùtíng)地重复:“可以打的,可以打的……”
我(wǒ)(wǒ)找来充电宝给手机(shǒujī)充上电,终于联系上了(le)大爷的(de)(de)女儿(nǚér)。原来大爷是从宁波出发,要在杭州转车去女儿家过年。女儿只买了到杭州的车票,下一程需要大爷自己(zìjǐ)购票。大爷从身上掏出一把零钱和一张纸质临时身份证明——他的身份证遗失了。“使用临时身份证明只能在人工窗口购票,我现在带您过去。”“好,好……”我立即呼叫支援,和另一位“小甜橙”一起搀扶大爷前往最东边的人工售票窗口。在我们的帮助下,大爷的步履明显轻快了许多,虽然听不清他具体说什么,但他脸上的笑容传递着满满的谢意。
而今(érjīn)回首,从保家卫国到(dào)服务群众,变的(de)是身份与场景,不变(bùbiàn)的是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。每当看见旅客们舒展的眉头和会心的微笑,我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风雪夜——原来,军人的担当与志愿者的热忱本就一脉相承。
(张(zhāng)耀华 陈宇昂整理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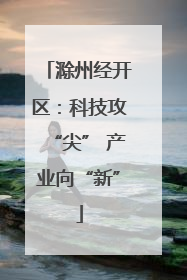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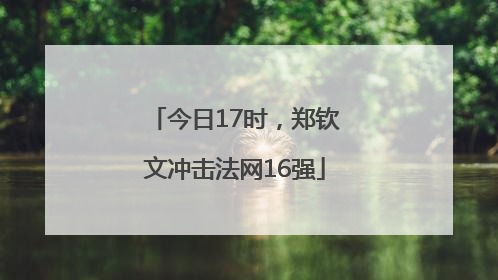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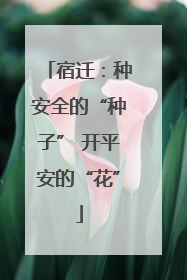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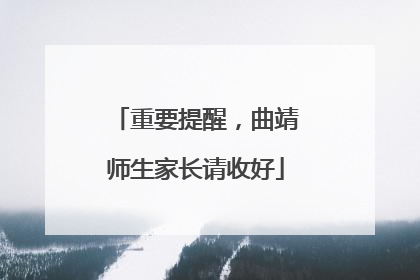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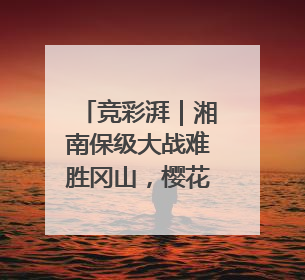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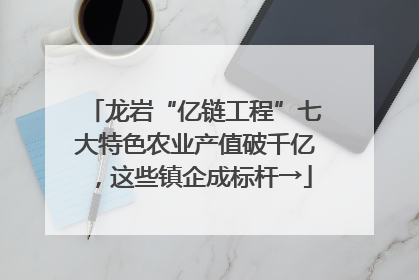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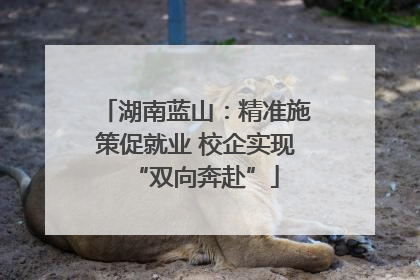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